初见欧立德教授,是在2015年4月由共识网周志兴老师带队的哈佛会上。那日欧老师出场,并不惊艳,我仅记住了他黑色羊绒大衣包裹下合体的西装和看起来略显冷峻的人面孔。但他一开口,我了:中文相当地道!为了显示对中方邀请人的尊重,欧老师全场用中文主持,不仅如此,他的反应还非常快,当听到周老师说:“我们没有完全按照老欧给出的题目来讲”,欧老师立刻略带委屈地回应说:“你们谁也没有按照我给出的题目来讲啊!”

每句话后带“啊”“啦”等词是欧老师的说话特点,这让他地道的中文表述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正式的味道,但他的神情偏偏又是严肃且高冷的,相形之下,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记得有一次一位师长因为给他写信总是收不到回复,嘱咐在哈佛旁听他课的我向他问询,于是下课后我拔腿追上教具正打算离开的欧老师,向他说明情况。他说回去查查日程表,然后给我回复,我诚惶诚恐地道谢,他则礼貌且客气地回应:“不客气啦!”轻柔的语调和这个“啦”,让我原本紧张严肃的心情瞬间放松,差点笑出声来。但看着他冷峻且严肃的脸,又强忍住了笑。
因为在日本留学三年,欧老师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说话声音(分贝)从来都控制在听者刚刚能听到的范围,且这种内在外化于外,给人一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感觉。当然他的语调轻柔也是因为年龄,欧老师是1959年的。这和我的合作导师宋怡明教授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宋老师因为年轻,中气十足,每次喊我名字声音大得都会吓我一跳。不过我很喜欢听宋老师讲课,不仅是因为他上课富有,神采飞扬、语词犀利、思想敏锐,而且因为哈佛的课堂上没有麦克风,宋老师的声音足够响亮,所以相比之下宋老师说的每句话我都能听清听懂,这也是许多上过宋老师课的中国学生很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到哈佛后我很关注哈佛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所以每场必听,而欧老师当时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心关于中国问题的他基本都会主持,其他学院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他有时间也会出席,所以我们常常相遇。我和欧老师的交谈是从某一天多次偶遇开始。那日周二欧老师结束课后,我赶去听中科院白春礼院长的报告,主持人又是欧老师。结束,我和几个朋友,晚宴结束,回来已经 9:30,上遇到欧老师、丘成桐和孟晓黎三位教授。校园的小径那么窄,我和欧老师并排向前走,他向丘成桐和孟晓黎两位学者介绍说我是班上的学生,然后询问我对白院长的看法。我如实相告:“中规中矩!”我看到欧老师用欣赏的眼神看着我,但是当听到我评论说:“我觉得白院长回答‘我们有百度’这句话没有问题!”他的神情突然变了。我理解欧老师认为我在为白院长,可是当我将我作为文科生使用百度的个人体验说完后,欧老师心悦诚服地点头。话题由此延伸开去,一直延伸到欧老师的家庭和学术……
现在回忆起来那其实是一段很短的校园小径,可是一上我们聊了不少话题,欧老师对中国问题的敏锐和对小不点学生的尊重在那一瞬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日的交谈后我们频繁相遇,欧老师每次都能喊出我的名字。他记人姓名甚快,我猜想这也是他为什么精通英语、法语、中文、日语、满语、蒙语等多种语言的原因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杜维明先生提出“文化中国”论说,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杜先生所说的“文化中国”包含三个意义世界:一是指由中国、、澳门、和新加坡地区华人组成的社会;二是由界各地的华人组成的社会;三是这一概念包括了一批与中国及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这其中既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汉学家,又包括长期与中华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从业人员和官员等——对于中华文化,他们是通过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加以了解的。在杜先生看来,以上不同团体都是文化中国的体现。
记得当时杜先生论文,我被这个概念吸引。进入侨务系统后,我一直在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去哈佛大学访问交流时拟完成的课题之一。受杜先生“文化中国”概念的影响,到哈佛之后,我对于杜先生提到的第三个意义世界中的个体亦相当关注,正是在这一支配下开始了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和专家的系列,通过深入了解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力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加深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做些工作。
在此思考下,我向欧老师提出的请求,欧老师邮件中回说:“好啊,给你半小时时间。”我说:“这点时间不够,至少要50分钟。”并以我赛奇教授的例子来说明——我赛奇教授用了50分钟,比较成功,还谈到文章出来后的发表意向以及我已向福斯特校长当面约访,她答应了。欧老师不语了。我再次邮件问起,欧老师回复说他已经询问过《清史研究》编辑部和哈佛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说《清史研究》不会刊登他的文章,而哈佛校长办也没有收到我要福斯特校长的提纲,他觉得我有撒谎的嫌疑。(他在英文邮件中没有明说,但我一读就明白。)我在邮件中反驳他,并毫不客气地请他直接去问福斯特校长。回完邮件我心里冷飕飕地,我想看起来如此儒雅的欧老师竟然猜测并背后调查一个学生,这让我对他的欣赏大打折扣。可是当我把电话打回国内时,我的心震撼了,特别是知道国内学界对欧老师的态度时,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欧老师这样对待我的原因。
那一刻坚定了想要欧老师的想法。我找来欧老师的《满洲之道》和《乾隆帝》细细品读,并下载了他的学术论文。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其实国内学界误读了欧老师!思考之后,针对国内学界之处和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写作了提纲,针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对欧老师的,我用问题还原了欧老师当时开展“新清史”研究的心历程,同时回应当前学界对欧老师的质疑。在中我将问题引申到学界对欧老师最质疑的“中国形成问题”;不仅如此,我还将问题延伸到欧老师的研究对世界历史研究的意义,以补上国内对其新清史研究的重要性较少关注的一面。
当我再次约访,欧老师没有凌厉的言辞,只是问我:“你真的确定要访我吗?”我言简意赅地回复:“Absolutely,sure!”那日,在他的新办公室(在之前他就已由费正清中心主任升为哈佛大学负责国际交流事务的副教务长),我去得很早,但是欧老师晚了。教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通他的手机,他才急忙赶来。我猜想他的脚步一定很迅速,因为我看到他的发型仍然保持着奔跑后的姿态。
最后时间远超出我想要的50分钟,事实上,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怕我听不懂,将问题展开来讲。他的思想颇有体系,可以从任一点开始,讲透彻后,在结尾处划下的句号。与欧老师,让我感觉他的“新清史”虽然从观点上来说尚未超出日本学者的论点和范围,但无论是对满文史料的应用,还是将其放界历史范畴内研究,都仍然有创新之处。特别是他从满洲八旗的民族性出发,运用族群理论,重新梳理清朝历史,发掘出前人很少注意到的清史中的一些重要层面,颇为有趣。

结束后,我没有再去打搅欧老师。偶尔几次去国际学生办公室办事,我过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透明的玻璃门,通常熄着灯。有次过我隔着玻璃门往内看去,看到他脱了西装外套,在未开灯的屋内靠在椅子上看书。我知道他的勤勉。想起某一日在东亚系的办公室对面听报告,我看到欧老师学生访他,知道他在。我舍不得腾出时间吃午饭,饿着肚子听到下午三点多钟,低血糖让我头晕,报告结束后就走出来捡起外面桌子上剩余的两块三明治中的一块(干干硬硬的),站在燕京图书馆的门前下咽。远远地,就看到欧老师从办公室出来了,他拿起我留下的另一块干三明治,然影一闪就回了办公室。那一瞬间我体会到的力量。
作为老师,如此天赋如此成就还如此努力,让学生情何以堪,唯有更加勤奋努力罢了。每天清晨,我沿着既定的轨迹在固定的时间穿行在去图书馆或教室的上,在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门前的道上和欧老师时常交错(他因为住房在另一个方向,所以去办公室要穿过校园小径)。那是一个深冬的早晨,欧老师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带着厚厚的翻毛帽子,他只顾盯着眼前雨雪泥泞的,竟没有认出我来,我快步跑到他面前,他这才发现我,笑容一瞬间绽放开来。他的笑容透着婴儿般的纯真,你很难想象这会是一个、审慎、敏锐的学者的笑容。我们聊了两句,他迈步前行,我望着寒风中他缓慢前行的背影,眼眶突然有点湿润。我想,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在他的记忆中恐怕早就应该淡忘了吧!
事实上,那天时我就知道欧老师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哈佛教育问题上。因为谈到中国时他的声音是完全平静的,只是在我追问:“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主任,您难道不想在此基础上为推动中国和哈佛之间的合作做一些努力?”他的声音才出了一丝激动。这让我想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新年招待会上,那天我们我再次相遇,他一见我就激动地问:“你有没有看春晚?”当我回答看了后,他立刻询问我的感受,并说他觉得(slogan)多了一点,我明白那时欧老师仍在关注中国动态。可是,看着现在为哈佛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如螺丝钉般的欧老师,我的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难过。可是站在欧老师角度思考——如他,在新的问题中找到新的研究兴趣,也是一种幸福吧!

临行前的一日晚间,我在燕京图书馆扫描借阅的英文图书,除了管理员和我,图书馆已未有他人,突然,一个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的人影走了进来——是欧老师,他来借阅图书。我快速按下扫描暂停键,一脸欣喜地跑到他面前。我们站着聊天,我向他请教语言学习秘诀,说到宋怡明教授还会中国地方方言,他立刻换了坏坏地笑容调侃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的中文不如你们宋老师好对吗?”我一瞬间涨红了脸。我向他辞行,并邀请他方便的时间来京和去高校报告,他答应了。我们握手告别,他的手凉冰冰的,可是当我望到他的眼睛里去,却看到他的眸子在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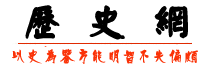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