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了解未界的大致,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世界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整个意蕴尚处于隐秘状态,还远没有充分地出来。要想了解未界的大致,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1789年5月,青年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在耶拿大学开设了一个。各地的许多大学生慕名而来,以至于先前安排的教室显得太过狭小,根本容不下众多热情的学子,校方不得不重新换了一个更大的教室。席勒所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普遍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
“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观念并非席勒首创,而是由康德提出的。康德于1784年发表论文《一个世界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特殊的现象,而是应思考人类总的发展进程,探测历史合理的发展规律。康德还提出了一个设想,认为历史自身或许存在着某种目的,“一项大自然的计划”,投射到现在之外,未来。
席勒当时不仅是声名卓著的诗人,也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席勒康德,提倡研究普遍历史。他在中谈到,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并非都是可以信赖的,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往往残缺不全,如果仅靠钻研“枯骨般的事实”,只能成为“尽可能狭隘的专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他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应研究“全部的历史”,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但他也改进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目标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席勒明确地提出,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现在的、经济、法律、教、语言、艺术等,凡此种种,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是专业的哲学家,同样也发展了普遍历史的观念,全面地研究历史。但在历史研究目的问题上,费希特同意席勒的意见,认为“现在”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各条线年,费希特在大学开设,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费希特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费希特提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渗透到它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去,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一个别的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费希特提出的“时代特征”这一历史观念,在过去200余年来,一直牢牢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际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包括“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新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也是康德“普遍历史”观念的者,同时还接受了康德的“历史有自身目的”的观念。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历史,将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而终结。他还,美国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极目标和最高阶段,是最完善的国家管理制度,未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有望持久的和平,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和平红利”。
有一种人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另一种人已经走得超过了自己的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地属于历史哲学问题,似乎超越了当今的时代。而在现实意义上,似乎又显得落后于当今的时代。过去一些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地发动和卷入新的冲突,很多人都认为“历史终结论”已濒于破产的境地。
相较之下,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接近于“现在”的时代特征。
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民族国家仍将继续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文明的冲突将全球。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代的战线。”
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益强大,并抵御其他文明,特别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这些大胆突兀的论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到了更为强烈的阻击。国际上许多家和学者感到极度不安,很多人亨廷顿,说他这样的论点是不的,国际社会应努力防止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强调寻求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共同点。
尽管“文明冲突论”潜藏着巨大性,但背地里仍颇为流行。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简直就是远瞩之见。学术与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总是试图领导,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所用。西方一些家和学者利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国际、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近两年来中东地区的动荡,都归咎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而为其军事干预和介入中东地区提供性。近年来,西方一些家对中国的崛起甚为,应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中国的,组成“神圣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而“文明冲突论”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是否真正有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有性,而在于其是否正确。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曾多次撰文亨廷顿,指出亨廷顿的观点是建立在“文明认同”这个模糊的概念之上的,而文明的本质在于多元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彼此相互尊重,而不是“认同”。
萨义德对文明的解释,深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关于文明的思想精髓。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一书中,对文明这个概念有过很细致的阐释:“文明”(civilizations)一词最早是在1732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原本是一个法律用语,即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判决,指称“”,与状态相对立。这个词在1772年之前传到了英国,取代了英文的“教养”(civility)。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具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意,用来指一个时期或一个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布罗代尔说,“文明”的确切含义,指某种为所有文明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即人类的共同遗产,如火的使用、文字、算术、种植和饲养等等。
布罗代尔还指出,文明本身始终是活跃的、不断变动的。“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像经济那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节奏,存在着波动和趋势,而且无论范围大小,总能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坐标。”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然而,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通常都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何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都会和某些东西。“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正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
真正的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尊重是双向的,而“认同”只能是单向的。如果一种文明单方面地“认同”另一种文明,势必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自行的倾向,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有实现的倾向。由此观之,“文明冲突论”的确是那种既极端错误又极端有害的理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文明冲突”都不可能是真正能够用做表述时代特征的概念。
布罗代尔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是康德、希勒和费希特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承者。布罗代尔将他的历史观称为“总体史观”,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大历史”,反映了历史学传统的继承、选择与摒弃,对当代历史学研究影响至为巨大。黄仁宇先生深受总体史观的浸染,强调要走出中国传统史学狭窄的界限,“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世界历史运动过程来的“大历史”。
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身体力行,埋首于浩繁的史料之中,呕心沥血,钩沉索隐,写出了多部历史巨著。其中,《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著名的两部。这两部著作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叙述了今天这个世界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柏拉图曾说过,方法决定结论。研究任何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其所运用的方法。布罗代尔不是直接地去探讨资本主义,而是首先从地理出发。“地理决定历史”这个命题,凝聚了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精髓。布罗代尔主张,历史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地理时间的历史,也称长时段的历史,一般以百年为段的地质学时间概念,来考察在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格局和气候变迁等。从这种地理出发,探讨人与其周围的关系史,探讨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历史是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第二个层次是人文时间或社会时间的历史,也称中时段的历史、“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中时段的历史具有局势性的特点,如、人口增长、资本形成、利率波动等等。在这个层次上应探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探讨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交换制度、市场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形态。这种历史在节奏缓慢的、几乎静止的历史之上,蕴含着最巨大的能量,如同深海中的暗流,掀动着整个社会的生活。
第三个层次是个别时间的历史,这是总体历史研究过程的最后阶段,也是传统历史的部分。这种历史不是整个人类巨大规模的历史,而是微观、个人规模的历史,是超出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上、以少数大商人经营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然而,这也是“所有历史中最动弦、最富有人情、最的历史。”但它们对历史的深层而言,只是“蜻蜓点水”。换言之,从总体历史来看,人们通常最为看重的各种和军事冲突,仅仅是世界文明长期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波澜而已”。
布罗代尔认为,在总体历史中,个别的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认为历史事件无足轻重,相反,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军事冲突,人们才可以研究历史。“每个历史事件历时无论多么短暂,都会带来,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还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没有这些,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由此可见,历史自身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不同时段必然只能由历史事件来划分,而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世界发展的进程,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而往往是历史的转折点。许多迹象都表明,今天的世界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和长时段历史研究法,已成为当代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袭了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但同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在其所著的《现代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和《历史资本主义》等著作中,试图用“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解释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构成成分和运行规律。简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包含三大部分:
其一,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从总体史观来看,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古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都形成了具有统一的体系的帝国,如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中华帝国等等,而现代世界体系则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也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由资本的无限积累的冲动所支配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现代唯一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起源于15世纪后期的欧洲,其历史性标志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最初时期,这一体系只是包括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和美洲的一部分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体系逐步向外扩张,并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卷入进来。直到19世纪后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这一体系。自此以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成正的、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其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任何体系性的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结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由于分工角色的不同,某些地区成为中心,其他地区则成为边缘区或半边缘区。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今天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均属于边缘区或半边缘区,处于这个体系的外围。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正以这种“中心外围”关系来支配着,这一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内部的交换方式是不平等的,总剩余的一部分从边缘或外围地区向中心转移,因而中心和外围之间关系始终是紧张的、不稳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将其不平等的交换方式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即使它的公开的敌人,也只是在这一机制运行500年之后,才开始系统地剖析它的真面目。
其三,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这一体系内在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系列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50至60年为周期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另一种是以100至150年为周期的霸权的波动。随着周期的波动,这一体系内的资本积累和的中心也逐渐有规律地发生地理上的转移,并导致维持世界秩序的霸权的更迭和控制方法的变换。
由上观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既承袭了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内容。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由布罗代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巨人支撑起来的。(未完待续)■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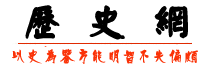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