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涛的丈夫
2018年10月13日—14日,“新史料与古史书写——40年探索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联合了《社会科学战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多个学术期刊编辑部,举行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学者们就新史料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的运用互相交流,因此不但参会学者以青年为主体,而且所提交的论文选题涉及的断代跨越了上古、中古史,还延伸到宋代和明清时期。
近40年来出土材料的与日俱增有目共睹,学者感慨其数量几可以超过此前的总和。概括言之,出土材料可以进一步分为出土文献和非文字资料,再加上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涵盖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新史料的很多方面,这些新出材料在本次会议上均得到了体现。出席本次会议的学者各自选题不一,而且人数较多,安排为两个分会场,因此报道只好介绍部分论文与学者们对会议主题产生的感想。为行文简洁计,学者姓名后均不加“教授”“先生”等称呼,敬请谅解。
上海大学赵争的《中国早期文献形成与流传模式问题略论》认为中国早期古书有两种不同的状态,源出官学的文献和语录体的诸子文献在性质、生成和流传过程存在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近来简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类新史料,其中有大量篇章与《尚书》有关,学者们称之为“《书》类文献”,赵争所说的源出官学的文献就是以《书》类文献为代表,他认为这类文献的产生和流传都具有制背景,因此较早地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于凯也关注早期文献,他的题目是《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古书所见早期历史书写体例及其分衍》,文中详尽地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简帛古书,就其中具有“史书”性质的不同文献探讨了其历史叙事的体例和特征。于凯也注意到数量巨大的出土材料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这说明早期历史书写的体例和流传是复杂的多元系统。
赵争和于凯对早期文献出土和研究情况的总结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就“《书》类文献”“涉史类古书”的范围如何界定各抒己见,有学者提出汉代以来的古书分类方法是否适用整理出土文献的问题。与会的谢维扬则指出出土文献本身无法表明自己是否有类别,我们只能根据一定的框架去研究,研究者自己对此应有认识。就古书分类的框架,学者们都认为是需要随研究进展而调整的,具体的细节则尚难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两位学者研究的是古书,新出土的文字史料中在此之外还有一大就是法律、行政文书,恰好大学沈刚的报告就是侧重这类材料,他在《出土文书简牍与秦汉魏晋史研究》一文中总结了简牍文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囊括从王国维、陈梦家等早期学者的开拓性工作,到最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出土文献研究,其内容详细全面令众多与会学者称赞。华东师范大学的章义和在总结这次会议时表示,学术总结是一项非常难的工作,不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是很难完成的,但这项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尤其是新史料和研究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他说这样的总结梳理堪称“”,对学术界会有很大的帮助。
“历史书写”在古代史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问题,不过类似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探究新史料中的叙事特征。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专门将“古史书写”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应是鼓励青年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开拓。
中古史的学者关注“历史书写”几成传统。中山大学的陈慧分析了甘宝在《晋纪·总论》这篇文献中如何为东晋的性张目,甘宝通过对比西周和西晋,褒周贬晋,又援引贾谊的《过秦论》,暗指西晋的历史命运,这样“从周”和“过秦”成为东晋可以借鉴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广西师范大学的江田祥发表了《岭南尧舜与南方历史书写》一文,在以前学者研究中古南方历史书写的学术脉络下,利用丰富的材料探究了尧舜向岭南地区的历史,他指出这一过程改变了华夏士人对岭南的文化观念,也提高了岭南的文化地位。
在出土文献日益丰富的上古史领域中,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新材料背后的历史叙述与书写问题。大学的鹏在《社会变动和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中认为西周晚期发生了表述主题的转变、表述内容的丰富和述作群体的扩大,有学者就文章题目指出表述和付诸文字可能是不一致的,只通过文字史料不能确定“历史表述”形成的时间,所以不妨直接借鉴“历史书写”的概念。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爱梅细致研究了简《越公其事》,她不仅指出这篇文献增加了越国及相关史事的资料,而且论证了其越国本位的叙事立场,楚人则因为其贬低吴国的态度也接受了这篇文献,并改写了其中对越国国君的称谓。师范大学的李锐则重点关注战国竹简中的古史文献,他总结了近代“古史辨”以来在古史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主张客观看待和使用新出土的史料,不能用“传说—信史”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评价中国早期文献中叙述的古史。
新史料的性质与内容各异,沈刚提到出土材料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在一些问题上具有文献所不具备的优势。章义和更认为新史料还具有开辟新研究领域的重大价值,他举例说古代中国的县政、基层管理问题,在新史料出现后就有了巨大突破,华东师范大学姚立伟的《秦边县迁陵中的尉》就根据出土材料提出秦代地方行政制度与汉代的不同之处。研讨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涉及各个领域,或是比较新史料与旧文献之间的差异,或是利用新材料探究过去未知或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示了用新史料回答旧问题、用新史料解决新课题的实践。
山会科学院的赵燕姣对西周时期的“东夷”“淮夷”进行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有多种看法,她根据古文字和考古资料支持淮夷是东夷从山东潍水流域迁到淮水流域这一观点。上海大学的王少林和西北大学的阮明套都是根据出土的战国文献,分别对《尚书·高肜日》和《尚书·金滕》两篇旧文献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武汉大学黄楼的《李翱〈杨烈妇传〉史实考证》一文指出《书·列女传》所收的《杨烈妇传》与出土的相关墓志有较大不同,他结合新史料与文献,重新梳理了相关史实,纠正了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并对不同文本之间的叙事差异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师范大学的凌文超从《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黄盖治理石城县的事迹出发,结合走马楼吴简了吴国的基层行政制度与管理模式。他表示自己关注吴简研究,一直希望从中提炼出若干制度,再与《吴书》等文献结合,这篇文章算是一次尝试之作。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啸以《杨勇的两个朋友圈》为题,结合新出墓志隋朝废太子杨勇身边的“文学”和“”两类人群,探讨了隋代废太子这一事件中的个人因素。刘啸认为根据墓志得出的结论与正史的记载也基本一致,提出应该注意在研究中不能轻易否定文献的可靠性。
出土史料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保存了很多旧文献不具备的历史信息,这使学术领域的拓展成为可能。华东师范大学的锋对西周时期的学校和教育制度展开研究,这一问题过去往往泛泛而论,他则充分结合青铜器铭文与文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朝阳利用长沙出土的东汉简牍,发现粤地和岭北地区经济往来的情况,以及长沙在汉朝南部市场中的作用。山东大学的孙齐在《芮城三百年史》中展示了一批6—9世纪芮城教史的材料,其中以造像为主,这让学者们颇为兴奋,徐畅回应道自己对造像也曾很感兴趣,但整体研究造像需要投入很多,非常困难,因此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复旦大学的白若思研究了江苏常熟地区的周神,除了利用碑文、宝卷等,而且有田野调查的基础,他还指出不同种类的文字史料是针对不同阶层的读者形成的。
这次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华东师范大学的章义和在总结发言上称赞会议论文“篇篇精彩”,在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外,更多学者对新史料的使用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多彩。此外,学者们对新史料的也值得称道,山东大学王晓鹏利用的姚河塬西周墓葬所出土的甲骨卜辞,华东师范大学刘啸利用的隋代墓志,均是今年才刊布的材料。
丰富的新材料也带来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近几年关于历史学研究中“碎片化”的讨论非常多。章义和说自己不喜欢“碎片化”这个词,更愿意称之为“技术主义倾向”,因为要解决新史料中的细节问题,难免采用具有“技术主义”的方法和观念,尽管有其弊端,但也有利于史学的进一步提高。凌文超在研讨会上提到,简牍研究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一)字句、(二)文书、(三)历史学、(四)社会科学、(五)哲学思辨。从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来看,大部分学者并不会自限于狭小的领域,多能起不同层次的研究,发挥新史料的价值。而且学者们对一些共同话题往往能够产生共鸣,尤其是在文献和出土史料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体会,沈刚、李锐等人均在论文里谈到了新史料亦有其局限,其他学者也通过具体研究展现了旧史料和新史料各有优劣。当谈到这一话题时,学者们往往都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
因此,章义和总结说,史学水平的提高需要提出好的问题。他肯定这次研讨会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指出也有一些新的问题值得共同关注。要想克服局限于新史料的弊端,就需要学者们建立整体的关怀,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对学者们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及时加以总结和交流,形成学术的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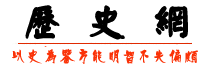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