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推文内容略有不同,为便于阅读,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感谢商务印书馆和王希教授授权推送。今天适值“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公号开通一周年,谨借此文感谢所有人的支持与厚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
196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使用过一句响亮的口号:“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人问题也是问题)。我想借它的语式来表示一个观点:“The historical is political”。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非所有历史问题都与相关——我想用它来强调,历史研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价值中立”,我们都无法否认,历史知识的生产是的产物,也注定是为服务的。美国史研究与教学在中国的发展正是这样的一种经历。
1784年,美国商船“中华皇后号”从出发,经过数月航行之后,来到广州,中国人从此知道了关于“花旗国”的知识。然而,直到200年之后,美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才在中国得以建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复杂的故事,牵涉到中国史、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以及相互之间的纠结。本文无意在此讲述这个故事,也不打算梳理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的流变,两者都超出了我的学识与能力。我仅利用这个机会勾画1949-2009年间美国史研究与教学在中国的变化的轮廓,目的是展示历史知识的生产(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与特定时代的之间的张力。我关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学家在知识与的博弈中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之所以选择1949-2009年是有原因的。这是中华人民国历史的第一个60年,以1978-1979年的“”为界可以分为两段。在前30年里,国家对文化和教育实行高度的统一管理,对公识形态的塑造拥有绝对的垄断权,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信息闭塞;在后30年里,中国实行,经济生活市场化、全球化的道,在价值观方面也出现了多元化,学术研究的空间大大扩展,国门大开,信息爆炸。中美关系在这60年里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从最初的相互敌对,接触与合作,再相互依存与竞争。所有这些都是特定时代的“”的一部分,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史研究与教学在中国的命运。
为讨论的方便,我把60年划分为3个阶段:1949-1979,1979-2001,以及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的背景和学术不同,中国学者习得美国史知识的动力和目的不同,知识的产出和影响也不同,但每一阶段的知识生产都有鲜明的“性”。
在第一阶段(1949-1979)中国的棱镜中,美国的形象是极为负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个形象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源自19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连串事件——包括中国人在的胜利、中苏结盟、美国国内的主义、朝鲜战争等——将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锁定在相互为敌的态势上。美国研究自然逃脱不了被“化”的命运。1951年为配合反美斗争的需要,《历史教学》连续发表文章,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种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中国学人对美国历史的一次密集介绍。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光是因为这些文章的学术性,还因为相当一部分出自归国留学生之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早期留美学生加入这种对美国的“”并不是盲目的或的,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利用专业知识来纠正国人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和当时盛行的“崇美”情结。
但这个集体行动并不预示美国史研究会成为新中国人文学科的显学。在百废待兴、新亟需巩固的1950年代,除了服从需要之外,人文学科的发展还受制于教育体制的设计。当时“美国史专家”(Americanists)——即受过美国史的专业训练并在大学讲授美国史的学者——的队伍规模很小,不超过10人,包括黄绍湘、杨生茂、刘绪贻、丁、刘祚昌等(前4人曾于1940年代留学美国并获得研究生学位)。他们已属极为难得的专门人才,但在当时没有美国史的课程可教。原因之一是美国史是隶属于世界历史之下的次级学科,而世界史本身在当时也是刚刚起步,在规模和学术传承方面不能与中国史同日而语。1952年仿效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对留下来的高校进行了重组,废除了大学和私立大学,历史学从此被局限在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之内,世界史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缩小,国别史则更没有发展成为单独学科的机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尽管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遵循高教部的于1964年建立了美国史研究点,并针对某些美国史专题(如黑人运动史)进行了资料收集,南开大学还制定了培养美国史方向研究生的方案,但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或史学领域的美国史研究在1979年之前并不存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美国史学者没有用武之地。事实正好相反,特殊的背景赋予这个小规模的美国史研究群体以特殊的:时代要求他们为了反美斗争的需要,写作时代需要的美国史知识,并通过大一统的教材和教育体系,将相关知识到全国的历史教学中,帮助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美国历史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也是一个施展才华和创造力的极好机会。黄绍湘教授和她的《美國簡明史》和《美國早期發展史(1492-1823)》最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
两部著作分别于1953、1957年出版,加起来将近80万字,篇幅巨大,内容翔实,由黄绍湘一人单独写就,即便用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也可以被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作品。黄著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的美国史叙事,提供了一种解读美国史的理论与方法。在《美國簡明史》的自序中,黄绍湘称,她“尝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讨论不同时期美国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及其后果”和美国的“对外的扩张和侵略以及人民的斗争”,从而展现“美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和没落,以及劳动人民的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规律。此外她的作品还借助了“美国的新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的分析材料为主要参考”,因而具有学术上的前沿性。从立场、内容到形式,黄著在当时都是不可多得的“正确”的学术佳品。
即便如此,黄著在当时也没有完全“垄断”中国的美国史知识的生产,学界仍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形式的美国史著作,尤其是从美国左翼历史学家和前苏联历史学家的美国史作品中翻译过来的译作,但最终作为标准叙事和解读进入全国世界史教材体制的仍然还是黄著。黄著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之后。若干年后,学界对黄著的评论——称其是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于沛语),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张友伦语)——并不是言过其实的赞誉,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可以通过黄著针对美国、美国、内战和新政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观点来看它的影响力:
·美国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激励全世界范围的运动”,“为全世界殖民地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例”,成为“美国社会进展的里程碑”,但”由于还未形成,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所窃取”。
·美国联邦是一部“保障剥削阶级的法律”,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巩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只有在“杰斐逊的督促和法国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才做出让步,在中加入了法案。
·美国内战“从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是一场“奴隶制和劳动制”之间的“两种制度的斗争”,是“美国‘第二次’”,对此马克思做了“天才论证”;内战“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形态”,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使美国具备了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条件”。
·重建“是资产阶级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以斯蒂文斯和萨姆纳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者”与“”之间的“两条线的斗争”;林肯在内战中“代表中间派”,他虽然颁布了解放宣言,但“始终还是具有的倾向”。
·罗斯福新政的“进步性是极有限的”,其进步性只在于“使美国避免了直接化的道,而以某种改良主义的方式,相当地缓和了经济危机”;新政的改良主义“与德意主义式的运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或的因素. . . .也没有任何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
分析法、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对的性和正当性的强调,以及对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发展的能动性的赞扬等,这些理论严格地说都不是黄绍湘的原创,而是当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黄的创造性工作在于她有效地运用它们来叙述和解释美国史。这实际上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对一个在美国接受过史学训练的人来说。仔细阅读黄著,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在处理美国、《宣言》、内战等问题时的理论挣扎。尽管她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定语来限定语境,但她仍然没有完全使用“”的概念,甚至对杰斐逊的主义理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参与写作通用世界史教科书的学者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美国史观来组织叙事。杨生茂教授主持编写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1962年版)也采用了阶级分析法,把殖民地时期描述成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时代,把“新兴的资产阶级”视为反英斗争的领导者。除了杰斐逊外,该书还将富兰克林也列为“杰出的(资产阶级)家和思想家”。《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在处理美国时,语气要比黄著略为缓和,认为它虽然创建了一个“的形式,”但因为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等而带有阶级和种族的标记。但在对美国内战的评价上,《世界通史》分享黄著的观点,将内战称为“第二次资产阶级”。
在“学术权威”被的期间,《简明美国史》和《世界通史》的“美国史观”并没有被抛弃。一部1972年发行、由广东省革委会编写的《世界近现代史讲稿》在“资产阶级世界”一讲中,引用论美国的语录,把美国战争称为是一场“资产阶级”。在讨论美国内战时,讲稿称内战前“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工人中”,促成“工业资产阶级”与“北部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最终导致了奴隶主阶级被。另一部近代史教材称“”是推动美国史发展的唯一主线。大学历史系于1970年代编写的《简明世界史》在讨论罗斯福“新政”时全盘接受了黄绍湘的观点(此刻黄绍湘在该系任教),将新政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有趣的是,该教材还驳斥了苏联学者对“新政”所持的正面评价,展示了当时的中苏交恶对世界史教材编写的影响。教材作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没有超阶级的”,而“苏修罗斯福,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的学说,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美化帝国主义”。无独有偶,在美国高涨的1968年,美国大学的一群激进学生也曾对在该校的苏联学者为罗斯福“新政”的表示愤慨。
195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学指南也使用“资本主义必然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将当时的苏联视为是人类历史的灯塔,而美国则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世界的主要堡垒”。一份1956年的高中历史教学指南对战争和内战的描述较为正面,但“美国形象在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中基本上是负面的”。
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教材使得这一阶段的美国史教学局限在几个“经典”题目上,如战争、内战、帝国主义、罗斯福新政等,并提供了标准的解读模式,其结果是,美国史研究与教学长期处于一种“”(fossilization)状态。中美对立使中国学者无法接触到美国学界的信息。1950年代冷战时期,唯一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是享誉全球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他于1959年作为中国的客人访华,并在大学发表学术,但他的题目是泛非主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史。杜波伊斯访问中国20年后(1979年),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教授来华访问。他也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时任大学的美国史教授、美国历史学会(AHA)。富兰克林的之一是帮助恢复中断了30年之久的中美学术交流,他也借机观察到当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某些侧面,并在自传中留下了记录。他注意到,在关于黑人史学的上,中国听众对黑豹党等“激进的或叛逆性的”黑人组织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等“主流”黑人组织的兴趣。他还注意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对美国左翼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著作可以如数家珍,但对黑人历史学家卡特·伍德森、查尔斯·韦斯利和雷福特·洛根等却闻所未闻。但令他感到颇为不安的是一位研究美国运动的中国同事对他说,小马丁·德·金曾提出“美国应该采用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这种对最著名的运动的立场的误读让他感到吃惊。幸亏当时他没有读到《世界近现代史讲稿》,不然他会感到。这部1972年编写的教材在讨论美国南部“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的起源时,称这些法律是“根据当时的议员、种族主义吉姆·克罗的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定的。种族隔离法的事实是铁定的,但这位“吉姆·克罗”却是凭空想象的,子虚乌有。这也许是一个无心的错误,但它不经意地为当时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中的“本土化”实践——按需要来“创造”美国历史——提供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脚注。
在中国的美国史领域的发展历程中,197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富兰克林教授的访华之外,这一年还了两件大事的发生: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成立,两者都关键性地改变了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的命运。中美建交开通了两国学术交流的和民间渠道,激发中国人全面了解美国的强烈愿望。美国史研究会则为专业学者提供了一个建构学术共同体的体制平台。该会在成立的时候不足50人,但在随后的30年里将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中最丰富的国别史专业组织。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之所以获得新生,如同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得益于国家于1978年之后在意识形态、追求和发展方向上的深刻转向:中国的核心内容不再是无止境的和对乌托邦社会的狂热追求,而是脚踏实地地追求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着“四化”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与教学也将围绕它而展开。
美国史研究会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撰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激动,”杨生茂教授多年以后回忆说,“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经过辩论之后,编写通史成为的共识。两位总主编后来写到,“由于以来的形势发展,我国急需有一种全面而非片面、系统而非零碎的美国历史的著作”。通史的最初目标是作为高校美国史专业的教材和通用的参考书,以“帮助人们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当今的美国。”什么是“比较正确”的认识呢?根据两位总主编的描述,新的美国通史“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既要“写出中国的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又要“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在]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思看上去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是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一种新的“客观”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如何做到这一点,则是对编者和作者的。
除此之外,由于长期与,研究者还面临资料缺乏、知识结构单一、知识老化、信息不通等问题。然而,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人才。1979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队伍规模仍然很小,主要包括那些从中存活下来的早期留美学人、1950年代派往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以及在前和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总共不到50人。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可以单枪匹马地完成通史的写作。然而,此刻正在恢复的研究生教育开始将新人带入世界史领域。美国史研究会决定采用中国的战略法宝之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突破——将该项目一分为六,由6所整体实力较强的大学各自承担其中一卷的写作。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通史的第六卷于1989年率先完成出版,第二、三、五卷在随后5年内相继出版。第一卷和第四卷的写作在初期困难,更换作者之后于2001年完成并出版。这样,全书从立项到总共近300万字的6卷本出齐,总共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参与书写者包括了三代人,累计35人左右(见表一)。
这项后来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学术工程的创作经历是一个值得详细书写的故事,因为除第一卷之外,其他5卷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时段也拉得较长,使用的资源也不尽一致,写作风格与思想深度无法做到一致,所以各卷的质量和学术含量高低不一。譬如,最先出版第六卷(讨论二战之后的美国史)是在1980年代创作的,当时中国的才刚刚起步,意识形态的“松绑”也刚刚开始,作者可利用的学术资源相当有限。5年之后出版的第五卷(讨论罗斯福及其新政)无论在材料还是在思上都更上一层楼。除此之外,作者在写作中还直接获得了研究罗斯福新政的美国权威学者给予的直接帮助。第一卷作者李剑鸣是临危受命,但于1995年接手后他获得了到美国收集材料的机会,所以他在写作中能够将美国学界关于殖民地史研究的最新纳入创作之中,而这些条件对于先前完成的各卷作者并不一定具备。如较早完成的第三卷在对美国内战史和重建史的讨论,使用的大多是1970年代或更早以前出版的材料,作者没有机会看到1980年代对这两个主题的新研究,更不了解其中的史学史变化。
尽管如此,6卷本《美国通史》作为一个整体无疑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历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在覆盖范围、结构规模、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它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部新的宏大叙事,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姿多彩的美国史画面,扩展了中国学者对美国史的研究视野,并尽最大可能在当时允许的下,提出了新的“正确”的美国史观。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对于美国,《美国通史》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认为战争的“最重要和最伟大”是在13个州里产生了“初步的共同的民族意志”,而美国“否定了传统的君主制和贵族,实行了资产阶级制,. . .在一定程度上了和防止”,使美国在后成为了“第一个真正实行资产阶级制的国家”。
·对于联邦,《美国通史》认为,从阶级性质来看,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其目的是“为了私有财产”,但它也是“美国所取得的的法律化和《宣言》中的原则的制”的表现;分立和制衡为“稳定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是“资产阶级史上的一次创举”。
·《美国通史》对美国内战的解读与传统的观点基本相似:内战“扫清了奴隶制度这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使美国资产本主义迅速发展,. . .[因而]被誉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美国通史》认为林肯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 . . .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他在解放奴隶问题上“了历史潮流,不失为一位建业甚丰的人”。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美国通史》全书中最具个性、最有理论色彩的修订。两位作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主义,而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空前重大的资本主义”;它的内容是“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旧制度的坏内容,“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样板”。
显然,《美国通史》在新旧美国史观中找到一种平衡。多数分卷仍然保留了一些关键的传统提法,如继续用“资产阶级”来形容和界定美国历史的相关事件,但作者们的指导思想有了关键的转变,不再将美国描述成为不堪、行将崩溃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开始承认美国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并具有的能力。因各卷覆盖的时段和主题不同,这种立场变化的表现也并不一致。在讨论工业化的第四卷和讨论罗斯福新政的第五卷中,突破的尺度明显地要大许多,尤其是第五卷,两位作者甚至专辟两章从理论上来论证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与历史影响。这种在观点上的“百花齐放”——实质上是新旧两种美国史观的并存——展示了书写者和编者在这个急速转型的年代找到一种既不全面接受又不传统解释的中间道。、对现代化的追求、中美关系的改善等,为书写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比较富有胆识和原创意识的书写者也希望通过书写来帮助界定新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至少他们希望将美国史研究从狭隘的“为纲”的中“解放”出来。
6卷本《美国通史》也推动1980、199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主题的多元化。美国史研究不再封闭在史、经济史的窠臼之中,而扩展至种族关系史、文化史、科技史、军事史、社会史、教史和大众文化史等,而现代化一度成为最大的热点。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西部史等,从无到有,开始兴起并迅速成长起来。这种发展带来通史、专著和论文出版的一个。根据李剑鸣的统计,从1979到1989之间大约有820篇美国史研究的论文得以发表,在此后的10年(1989-2000)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在1978-1988的10年里,有17本美国史专著得以发表,但在此后的10年里,美国史专著出版的数量达到了80部。
这一阶段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也对传统的美国史解释有所修订。譬如,1992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在继续将美国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同时,也称它是“一场伟大的”——“”不再只是属于“资产阶级”;1787年制定的美国“帮助防止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内容包括“政体、民选、文官对于军队的崇高权威,以及的修订程序”等;美国内战是“一场成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废除了“奴隶主的”,“激发和帮助工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迅速而全面地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有效地推进了美国劳工运动”,并”为美国黑人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高中历史教材中的世界史和美国史观的修订速度较慢,但频繁发布的中学历史教学指南说明也透露了修订高中历史教材的紧迫性。1992年颁布的历史教学标准将美国战争与英国和法国并列为“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1996年颁布的中学历史教学课标接受了6卷本《美国通史》的说法,将美国视为“民族的解放”。1980年代的高中世界历史课本均对罗斯福新政采取了较为正面的评价。总之,这一时期中学历史教材中的美国形象也从“头号敌人”变成了“头号强国”,中国必须与其打交道,但我们需要对其“保持”。
这一阶段也了中国的美国史方向研究生教学事业的起步。在这方面,6卷本《美国通史》项目的实施做出了关键的贡献。通史项目启动的时候正是研究生教育在高校恢复的时刻,早期的留美学人——杨生茂、黄绍湘、丁、刘绪贻等——抓住机会,建立了美国史方向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并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等相继建立美国史或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也得以建立),为研究生培养打下了体制基础。换言之,在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30年之后,美国史教学获得了自己的体制轨道。
然而,即便是在南开、武大和东北师大这样的学校,研究生教育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从课程设置、培训方案到标准的建立等,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此刻,6卷本《美国通史》为最初的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训练机会。当通史的各卷分配给各校之后,资深学者负责设计写作大纲,然后邀请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参与研究和写作。曾对参与写作《美国通史》第三卷的经历感激不尽。他起初对自己负责写作的城市史一章并不精通,但在导师丁的指导下,通过大量阅读和研究,不仅完成了写作任务,而且还将城市史变成了自己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第二卷主编张友伦教授回忆说,南开大学的通史写作团队也包括了研究生,使用的方法也与东北师大相似。当时南开并没有一整套现成的美国史课程,而都是根据导师的研究题目来设计课程。张友伦当时开设的3门研究生课——美国劳工运动、西进运动和19世纪美国史——都与他当时的研究密切相关。张友伦的学生李剑鸣回忆说,研究生时代的写作专业训练主要来自自己对优秀的史学作品的反复研读和模仿。
在这一阶段,美国历史学家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后第一批到南开大学的美国学者海曼·伯尔曼(Hyman Berman)、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带来了上百本美国史著作。其他在1980年代来访的历史学家——包括赫伯特·戈德曼(Herbert Gutman)、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汤普逊(E. P. Thompson)——也传递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信息。中美间的学术交流还采用了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如1991-1995年间在美国驻沈阳馆的协调下,东北师范大学先后举办了5次电话学术,中方学者和学生通过电话与美方学者进行问答式交流。美国史研究会在1990年代的年会还邀请美国学者到会分享研究。2000年包括南开大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5所国内大合邀请美国历史学会、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访华。此外,富布莱特学者交流项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福特基金会等也提供难得的机会,安排中国学者前往美国高校访问和做研究,或提供出版资金。早期赴美的中国学者则充分利用机会,追踪美国历史学界的,并在回国后及时将访学成为教学内容,创建美国史的课程设置。无论是老一代学者、中生代学者、还是新生代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心的工作,当今美国史研究生教学中的一些新领域和新课程,如城市史、殖民地史、早期文化史、妇女史、数字史学等,与这些学者的用心是分不开的。出访与交流虽然是个人行动,但因为行动者具有高度的专业力、良好的专业训练,并分享一种因参加通史写作这样的项目而获得的集体责任感,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捕捉到高质量的专业信息,并在回国之后通过他们占据的有利将一些想法付诸实践。这也许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教育为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从无到有、迅速成长的“秘密武器”。研究生队伍的成长带来美国史研究队伍的壮大,到2011年时,美国史研究会的登记会员达到400多人。
我选择2001年作为第二阶段的结束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一年,6卷本《美国通史》的最后两卷(第一、四卷)完成出版,其中包括李剑鸣教授写作的《奠基的时代》。这一卷覆盖了从殖民地时期到战争开始的美国历史,按历史时间顺序,是6卷本第一卷,也是全书中唯一一部由单个作者完成和署名的一卷。这一举动并非有意事先安排的,但它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具体说,它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那个正在结束的时代中,学者们必须在新旧意识形态的话语之间挣扎以寻找一个平衡点,人们喜好进行大规模的学术创作,协同作战,集体攻关,将个人的贡献融入在集体的成就当中。而正在来临的时代则更多提倡的和个性化的学术创作。《奠基的时代》象征了时代的交替:它孕育于一个集体项目的宏大思考之中,但从研究到写作都展现了一种极为精致的个人风格。
理论上,《美国通史》应该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读者的美国史标准读本,但21世纪初中国和中国学界的迅速发展改变这一预期。中国在加入WTO之后(2001),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全面展开,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与外部世界(包括美国)的相互了解的速度加快、要求变高、渠道增加、程度变深。这一切美国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快速成长,不再围绕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体系而展开,也不再由某一个学者或某一群学者为研究主力;研究内容和主题变得更加多元化,不再是仅限于传统的史和经济史,而即便史或经济史的研究,也不再局限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题目,一个新的研究和一种新的研究心态开始出现。
如果说第一、第二阶段的美国史研究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美国要么是“头号敌人”,要么是“头号强国”——研究和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新的美国史研究是一种对知识的纯粹的追求:美国是万国中的一国(a nation among nations),美国历史是一种独特的、但并不例外的人类经验,既不需要对其膜拜,也没有必要嗤之以鼻;研究美国历史不是为了捍卫或某种指定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是为了某种上的需要而要给其贴上某种标签。换言之,对真实的美国史知识的追求、对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客观思考和判断,成为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所追求的学术目标,也是他们的“”。比起他们的前辈来,他们努力避免对美国史采取一种非白即黑的简单化的态度,更希望让史实而不是让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说话。
在这一阶段,研究生的专业训练开始变得更加规范,训练体制有明显的改进,对研究生教育体制的财政投入也明显增强,研究条件和也大为改善。一方面,美国学者来华的机会增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与美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美国历史学界的优秀作品开始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不光是通史著作,也包括专题研究。最大、最关键的变化是研究资源的数字化和电子化的速度,凭借数据库和网络,研究生不仅可以较快地阅读到美国学界的最新创作,而且可以通过高校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和美国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源直接接触到研究所需要的原始文献。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和中国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出国项目获得了到美国做原始档案研究的机会。他们通过这些机会,直接接触到美国学界的前沿,并与同领域的美国学者进行直接对话。此外,国内的业内交流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闭门造车的情形大大减少。所有这些变化在2001年之前是想都不敢想象的,也使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的训练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自2009年开始,我亲眼目睹了大学美国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在选题、研究材料和写作方面发生的质的变化。我注意到,这些论文在选题时所参照的学术史标准,不再是中国国内的美国史水平,而是国际学界的美国史水平。在这种背景之下,6卷本《美国通史》作为参考书和学术指南的有效性便受到了挑战。事实上,这套书作为一个整体在大学通史课上的使用也受到了挑战。这可能是作者们始料未及的。
我们可以从近期出版的专著(大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题目和近几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来窥见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见表2-4,推文省略)。
这些选题大多比较细致,领域也非常广泛,虽然美国对外关系仍占有较大的比例,但也有学生进入到南部史、城市史、移民史、女权运动、非裔美国人史、商业史等领域中。的表格也显示,论文选题与博士训练项目的学术传承(包括博士生导师的特长)有很深的联系。譬如,厦门大学的美国史研究以城市史见长,东北师大则以移民研究见长,南开前几年的师资较为雄厚,学生选题也较为多元化。
博士论文选题的多样化和细致化,说明学科发展在不断趋于成熟。2010-2011年的学科调整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并列为一级学科,给美国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美国史隶属于世界史、世界史并不享有与中国史同等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美国史方向的博士生进入高校历史系任教,各大学开设的美国史课程的机会在增加,美国史教学和教材的多元化也将出现,但这些距离美国史作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显学的出现还有很远的距离。显学的基础并不在,而在于是否能建立起一种不光对本学科而且对相近学科都有持续影响力的方。
6卷本《美国通史》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到了中学的历史教材之中。譬如,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述“美国的建立”时,就直接采用了《美国通史》的说法,指出“等美国资产阶级领导人”为反对君主制、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制”作出了努力,认为带有“分权与制衡”机制的美国联邦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为. . . .体现了一定的”。同本教材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直接照搬了6卷本《美国通史》的观点——新政“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 . .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 . .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保障,. . .使美国避免在危机形势下道,. . .对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即便如此,中学历史教材中的话语权也不再仅为教材编纂者所垄断。譬如,针对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将“联邦制”解释为“集中”的写法,两位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他们认为,美国联邦制的核心是“和地方的分权”,而不是中央,而“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是“美国试验得以成功的”。又如,在准备美国内战的课程设计时,另外一位中学教师希望另辟蹊径,“挖掘出这场战争所蕴含的现代宽容”。她决定将邦联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引入讨论,学生思考他为何“明知南方错误,明明反对奴隶制,却依然为南方而战”。李将军拥有的地域忠诚感“与我们所的‘灭亲’的传统价值观大相径庭”,因此可以用来“拓展学生认知历史的视野”,“感受美国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突破固有的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从1950年代《美国简明史》对南部奴隶主的无情到21世纪年轻的中学教师对李将军的价值观的“理解之同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美国史教学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上述的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至少可以总结两点。首先,美国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十分年轻,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教学的历史则更短。第二,虽然时间不长,但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经历一个从“极端化”到“弱化”、再到“去化”的过程。所谓“去化”不是说研究者不带立场或判断,而是说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不再受某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者和教师开始拥有了较大的进行思考和做出判断的空间。换言之,美国史研究的“性“并没有,但“”的内容改变了。
未来与前景何在?全球化的进程将进一步激发中国内部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变化,世界史被调整为一级学科彰显了伴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需要透彻、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的紧迫感,美国史作为一个国别史领域也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成长。但这种期望能否实现仍将受制于几种现实。
第一种限定来自体制方面。目前很多大学历史系中的世界史教员人数较少,讲授美国史的专职教师更少,一般只有一人,许多情况下,连一人都没有。拥有3名或3名以上专职美国史研究者的历史系不超过5个。除非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人数的规模将世界史和美国史领域的生长。换言之,如果世界史与中国史的教师人数能够在全国所有的历史系(院)做到平分秋色,中国高校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水平将不仅达到并会超过现有的世界水平。
第二种限定是学术方面的,主要与研究生训练的程序与质量有关。前面提到的从第二阶段(1979-2001)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代人是极其优秀的。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自身的、勤奋和志向获取的。他们从老一代人手中接过了培养人才的重担,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铺搭桥的贡献。但目前进入研究生项目的一代人虽然有较好的和条件,能否成才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以整体的规模接受到第一流的训练。这种训练的内容包括从事原创性研究的思想能力和文字能力、对国内外学术传承与动态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数据化时代对新旧形式的史料的获取与使用。做到这些,需要一套严格的、有序的、富有逻辑感的课程设置,辅之以具有健康的专业学术氛围的学术共同体的支持。目前,这套体制并不存在,自古以来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依然是训练学生的主要模式。
第三个限定与“”相关。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国史?中国人应该如何学习美国史?为什么的问题比较好回答,如何的问题则比较难。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在纠缠中国学者。前人也一直没有停止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法。今天这种努力仍然在继续,但大多数的学习者在专业上仍然继续跟随美国学界的步伐。这也不奇怪,美国以外的美国史研究者似乎都是如此。问题是,这个过程需要延续多久?会不会导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殖民化”——即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最终不过是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汉语版?国内学界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带有复杂的心理,除了担心学术性之外,还包括了创建中国特色的学术的强烈愿望。主张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愿望和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弄清楚几个问题:“本土化”是指立场的本土化还是方法的本土化?“本土化”本身会不会被“化”——即“本土化”的学问就是好学问?谁来制定“本土化”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在立场上是本土化的,但在方法和材料上却本土化的,那他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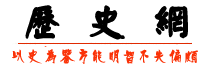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