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听见她拽线嗖嗖的声音,再不做鞋纳鞋底的声音。等到我早晨醒的时候,我首先闻到饭菜的香味。跟着我娘,从来没让我吃着一点苦。
2005年的一天,一位头发斑白的日本老妇人出现在中国东北火车站的站台上,她要探望一位曾经养育了她四十一年的中国妈妈曾秀兰、看一看久违了的第二故乡。
听我二哥说,我们是1944年随着八丈岛开拓团来中国的开拓移民。我哥说那时候,动员老百姓到东北来开拓移民。
为了达到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东北、东北人民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开始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对于他们来说,加入满蒙开拓团,就是去一个遍地大豆、高梁,如同天堂般的地方。田山昭子的父母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举家来到中国的。
殖民的梦想最终在他们来到中国后的第二年破灭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2日,在密苏里舰上签署投降书,期间日本军队向各战区的中队交出了武器。而没有了日本军队的满蒙开拓团四处溃散,他们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们身边的孩子便成了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附近的孤儿;还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于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旁郊野,任狼撕狗扯;更有甚者,当时的一些死硬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溃逃中对自己的实行集体,侥幸不死的孤儿被中国人抱回家中抚育。
在中国,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许多中国老人,提起当年日本人撤退时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75岁的于泾老人说,当时好多日本人,没有能力再带孩子走了,他们就只好把孩子扔掉或者是送人:
当时特别是外地的日本人,从远道来到的这些日本人。他没有能力再带孩子,他还没有吃的东西,他又没有住的地方。这些人在沿途上就只好扔孩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吃的,孩子会饿死。这样他要跑,孩子怎么办?他就扔。有的能讲汉语的人,就哀求中国的老百姓收养他的孩子。没有这种能力,情况特别紧急,他有的就干脆扔到道上。
战争结束了。那时候我小,也不太知道啥,就知道我妈死的时候,我还跟她在一个被窝里。早晨才发现我妈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把我们姊妹就分别(交给)中国人来收养。
在曾秀兰家,田山昭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还得到了养父母给她起的中文名字平。几十年后,曾秀兰谈起这段经历时平静地说,这孩子那时候就在街头流浪,我们不要她,她就没有活了。瞅着让酸,我是个女人,也当妈呀!
都拉扯三四个了,都说不想要了。我婶给我送来了,老头乐意,说这么大养活着呗。就(把孩子)留下了。
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即使我在日本而她在中国,田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和田山昭子一样,战后,有五千多名日本孤儿被中国人收养,他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刚刚出生几天。在生与死的变故中,他们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到了养父母家,上下衣服都给换新的,而且给我洗呀。那个时候头发比较黄,就给我把头发都剪掉了,为了长出新头发。到了这个家,我就感到,不是到了一个陌生人家。好像是有缘份吧!
我妈把以前的留起来的绸缎,都不是大材料的,绿的、蓝的,绸缎啥的,就给我做上新衣服上学。鞋什么的,也都是我妈亲手做的。我在穿戴上,比一般的人家还要好。
那个年代,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女孩是不需要上学的,相夫教子是一辈子的职业,曾秀兰却毅然把田山昭子送到了学校。
我上学的时候,亲属也有争论,背后对我妈说,一个丫头蛋子,还供她上学干什么,将来都是人家的人。我妈说,就是丫头蛋子也是人,她既然能考上我就得要供她。
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上学得过条河。有的时候下大雨,河水涨了,涨了以后过桥就挺的,我就记得我爸,我放学的时候去学校背我回来,后来我一想起来吧,确实是好像比亲生父母那种感情还深。
田山昭子的经历并不特殊,现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盐原初士也是战争遗孤,至今还记挂着中国亲人对她的养育之恩。
我祖母都吃酒糟,就是制酒剩下的酒糟和豆饼掺在一起蒸窝窝头,就是带眼的窝窝头吃。给我把高梁米磨成面,烙成小饼给我吃。这是使我难忘的养父养母的恩情。当时我的祖母吃这些东西都吃得拉血,他们也不舍得吃一口细粮,把这些粮食都省给我。我能活到今天,就是这些中国人把他们的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能活到今天。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永远不能忘记的。
1972年9月2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的手与中国总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9月29日,中日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日两国从此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一些日本遗孤被陆续找到了。70年代中后期,这些日本遗孤陆续告别了中国的养父母,开始返回日本。
后来慢慢地试探着跟我妈讲,说要回日本探亲,不是在那边永住。看看我妈同意不同意呀!我妈挺的,也没啥说的。我说我还回来呢,也不是说永远就在那了。
临到走的时候,我们孩子走,我家先生走,都不能让她亲眼看见我们走出。那(妈妈)她的心是受不了的。
六十年前,是善良的中国养父母向这些身世悲惨的日本孤儿伸出了慈爱之手,用心血把他们养育,而现在,又是这些善良的中国养父母,着离别之苦,将陪伴他们几十年的孩子送回故乡。和田山昭子一样,日本遗孤盐原初美也曾经着相同的痛苦:
我父亲来信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电线行。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希望能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全家拿着这封信呜呜地哭。两个孩子就受不了了,说把我们的姥姥姥爷接过来吧。从那以后,我就请求日本给我爸爸妈妈办手续。他们说,我们也不缺钱,也不缺吃不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
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中国,这是很多日本遗孤都要说的一句话。因为工作原因,田山昭子不能经常回中国,每一次回来她都觉得时光短暂。吃过晚饭,她一边陪着养母曾秀兰看,一边帮养母洗脚。
没到点呢。过几个月就回来了。你就好好保重身体,不用惦记我。回家也不用着急,别让你姥姥下来了。
田山昭子再次母亲不用下楼,而养母曾秀兰始终放心不下,在众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楼,一直站着,望着女儿的车,看车子渐渐走远……
我就总在她耳边喊她,她也不,后来做了几次人工呼吸也不行。最后的时候,大夫看她的眼球,她都没什么(反应)。大夫走了以后,我也扒开(她的)眼球瞅一下,她这时候就流泪了。我就觉得她知道是我,但是就是叫不回来我妈了。也就是这样,我养父母也没了。亲生父母也早就没了,养父母也没了。我也就真的成了孤儿了。
当年,遗留在中国东北的5000多名日本遗孤,如今已经有2400多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中国养父母的胸怀和的爱使他们终生难忘。
盐原初美,中国名杜冬梅,1945年被养父杜凤山、养母于世芬收养。时年4岁。1992年,盐原初美返回日本。
堀越一美,中国名,1945年被养母尤桂芬收养,时年1岁。1986年,堀越一美返回日本。
青山百惠,中国名徐桂兰,1945年被养父徐凤山、养母李淑贤收养。时年3岁。1990年,青山百惠返回日本。
吉田达男,中国名张顺富,1945年被养父张芳礼、养母禹桂荣收养,当时只有3个月。1989年,吉田达男返回日本。
山川文武(于华春),1945年(4个月)被养父于志福、养母高收养,1985年返回日本。井原禾子(),1949年(5岁)被养父张森、养母范玉芳收养,1989年返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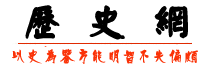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