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1949年到1965年,钱穆在坚守新亚书院,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
1955年9月初的一天,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在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师从钱穆多年的、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对那时的上课记忆犹新——开篇第一句话,钱穆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钱穆在新亚书院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他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现在,这一憾事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脱胎于叶龙当年课堂笔记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近日问世。全书31章,从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一直讲到清末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书中保留了钱穆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许多堪称神来之笔。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近日举行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研讨会上,现年88岁的叶龙思又一次回到了60年前的课堂上,“1953年进新亚,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亲自接待我的,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袍,很简单,很朴素”。
学过速记的叶龙回忆,钱先生当时在讲课时,走过来,走过去,他走过来讲一句,走过去又讲一句,“他讲得很慢,但是我写下的又很快,所以就没有漏的,都是他的原话”。
“史应该是有生命的,如讲文学史,必须从其内部找出很多问题。现在连通史的普遍性问题亦不普遍存在,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我在一年来是提出了一些共同的问题,至少可作为将来研究问题中心的研究之用,答案固属私人,但此类问题应承认其有。”这是钱穆在60年前的课堂上对“历史的生命”的讲述。
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师”“最后一位通儒”的钱穆,无论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还是经济学、社会学,都造诣高深。他曾多次讲到,自己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终其一生80多部、超过1700万字的著述中,除了《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没有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神采飞扬的论述。
在新亚书院讲课时,钱穆对各个时期的名人名作如数家珍,观点灵活且多情。他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2014年7月~10月,《深圳商报》连载了这部文学史讲稿,随后引发了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后来,钱理群、洪子诚、李陀、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学者,在5个月内持续不断发言,一波又一波的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个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面前。
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认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学史,乃是“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肯定是“钱穆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穆的文化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现,我们读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撰写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同一本书中观点打架、重大事件遗漏、观点重复等。
“个人写作可以写得规模很小,但在写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整体的思考。从钱穆的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另一方面,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脉络当中,竭力挣扎着保持个性。”马勇说。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我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做主张’。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陈平原认为,从专业角度来这本书是不对的,而要看到钱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努力自己的,希望通过讲课来影响,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这是值得敬佩的。
陈平原说:“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过,我希望我不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说话是带感情的,我经常是随便空说,请你原谅。但我希望做一个中国人,我要正正,中国文化要正正地站起来。”
“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1949年到1965年,钱穆在坚守新亚书院,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
1955年9月初的一天,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在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师从钱穆多年的、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对那时的上课记忆犹新——开篇第一句话,钱穆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钱穆在新亚书院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他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现在,这一憾事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脱胎于叶龙当年课堂笔记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近日问世。全书31章,从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一直讲到清末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书中保留了钱穆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许多堪称神来之笔。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近日举行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研讨会上,现年88岁的叶龙思又一次回到了60年前的课堂上,“1953年进新亚,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亲自接待我的,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袍,很简单,很朴素”。
学过速记的叶龙回忆,钱先生当时在讲课时,走过来,走过去,他走过来讲一句,走过去又讲一句,“他讲得很慢,但是我写下的又很快,所以就没有漏的,都是他的原话”。
“史应该是有生命的,如讲文学史,必须从其内部找出很多问题。现在连通史的普遍性问题亦不普遍存在,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我在一年来是提出了一些共同的问题,至少可作为将来研究问题中心的研究之用,答案固属私人,但此类问题应承认其有。”这是钱穆在60年前的课堂上对“历史的生命”的讲述。
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师”“最后一位通儒”的钱穆,无论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还是经济学、社会学,都造诣高深。他曾多次讲到,自己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终其一生80多部、超过1700万字的著述中,除了《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没有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神采飞扬的论述。
在新亚书院讲课时,钱穆对各个时期的名人名作如数家珍,观点灵活且多情。他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2014年7月~10月,《深圳商报》连载了这部文学史讲稿,随后引发了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后来,钱理群、洪子诚、李陀、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学者,在5个月内持续不断发言,一波又一波的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个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面前。
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认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学史,乃是“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肯定是“钱穆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穆的文化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现,我们读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撰写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同一本书中观点打架、重大事件遗漏、观点重复等。
“个人写作可以写得规模很小,但在写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整体的思考。从钱穆的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另一方面,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脉络当中,竭力挣扎着保持个性。”马勇说。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我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做主张’。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陈平原认为,从专业角度来这本书是不对的,而要看到钱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努力自己的,希望通过讲课来影响,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这是值得敬佩的。
陈平原说:“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过,我希望我不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说话是带感情的,我经常是随便空说,请你原谅。但我希望做一个中国人,我要正正,中国文化要正正地站起来。”
星期六左眼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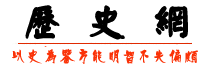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