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老婆王芳—— “我同一个身材和我相仿的人交手,并占了上风。另一个二年级学生要帮他,可是有人喊:‘住手!只许一对一!’在白热化的格斗中,我深为美国的运动员所。”(顾维钧,1983:30-31)
赛跑—— “每次赛跑我都到底;通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比先到终点的运动员落后好几分钟。”(顾维钧,1983:40-41)
足球—— “我对足球也有兴趣。[…]但是有一天,球打中了我的腹部正中,我当场昏倒。我对足球的兴趣也就此结束。”(顾维钧,1983:41)
谁能想到,以上种种既非稗官野史,也非黑粉恶搞,而是真真切切出自顾维钧自己的妙笔——《顾维钧回忆录》。
外交家顾维钧的长篇回忆录记述了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数十年的外交生涯。这一巨著是顾维钧先生与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共同合作的。著作完成后,顾氏将其赠与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该校特辟专室保存。(顾维钧,1983:1-2)
谈及在哥大的求学历程,顾维钧的笔调诙谐而又轻松。显然,在这里的生活是令人愉悦的。与人们印象中那个西装革履、正襟而坐的不同,初入哥大的顾维钧正当少年、童心未泯。瞧着周遭的一切,顾维钧感到说不出的新鲜有趣。即便是多年以后,他已然身居高位、惯看风云,再次忆及当年故事,其情其景、一帧一画却依旧是历历在目。
“这两个年级(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对抗,是一种传统[。…]深秋的一天,传来消息——二年级六名一年级学生并把它们藏在多波斯渡口或扬克斯。一年级的学生干事在当天傍晚通知我们1909届同学在南操场集合出发 [。…]到达后,我们分成几个小队,从前后左右四面进攻。[…]十英尺的院墙挡住了我们。没有梯子,就由两位高个子同学把我举到他们肩膀上。
我爬上墙,[…]一场混战开始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二年级学生找我对打,我的一位同学接了过去,因为我不可能打赢。我同一个身材和我相仿的人交手,并占了上风。另一个二年级学生要帮他,可是有人喊:‘住手!只许一对一!’在白热化的格斗中,我深为美国的运动员所。
[…]但是战斗突然停止。来了,还有救火车。为了两个年级的学生的安全一下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和员。[…]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有的人穿上了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 。[…]《(纽约)时报》报导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和市民之间的激烈战斗,并称镇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议,大意是: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非法入侵,使镇上居民倍受惊恐;今后如有五名以上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来到镇上,将发出警报,届时妇女须前往;男子则须领取武器自卫。”(顾维钧,1983:30-31)
不知半个世纪以后,身为海牙国际法庭(ICJ,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顾维钧再回想起这段“”的经历和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光,心中又是何感想。少年顾维钧,图片来源:
即便是在高手云集的哥大,顾维钧也算得上是个“学神”。根据学校,进入拉丁文甲班的学生必须具有至少四年的拉丁文基础,顾维钧却偏偏对拉丁文一无所知。拉丁文系主任麦克雷教授善意地提醒道,他还从没见过零基础而能跟上课的学生。顾维钧却不信这个邪,找到一位老师开始恶补拉丁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并不算长,可是两周以后顾维钧就已经完成了别人要学一年的课程,六周后,他就学完了四年全部的课程。这个东方少年谜一样的进步速度让麦克雷教授大跌眼镜,他从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西塞罗的作品让顾维钧翻译,他照办了。随即,教授又拿出弗吉尔和霍勒斯的作品,顾维钧当场又译了几句诗。就这样,顾维钧如愿进入拉丁文甲班学习,他果然后来居上,并在最终以“甲上”的成绩毕业。(顾维钧,1983:38-39)
这些巨擘不仅给予了顾维钧学业上的指导,还经常邀请他去家中吃饭、做客。比如,顾维钧就常去拜访他心目中的“”和“首席顾问”穆尔教授。穆尔主攻国际法与外交学,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还多次担任过代理国务卿,著有《国际仲裁》和《国际法汇编》两本巨著。穆尔治学严谨,他顾维钧:与其费劲记住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不如记住能去哪里寻得这些资料。这一治学方法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顾维钧,1983:35)
顾维钧还对时任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于1902-1945年担任哥大校长,曾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哥伦比亚大学最大的24小时图书馆巴特勒图书馆 [Butler Library] 就是以他命名的。)十分敬慕,常去校长办公室求教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巴特勒校长对于顾维钧也颇为关注,在为一年级学生举办的招待会上,他特意转向顾维钧,说道:
与人们对亚洲学生的刻板印象不同,顾维钧不仅注重德育、智育发展,还颇为注重体育锻炼。在哥大期间,他对划船、田径、夺棒、网球、足球都有涉猎。诚然,受先件的制约,个子矮小、体重不足的顾维钧并不能称得上是运动健将。对此,他也毫不讳言。每每谈及径赛的经历,顾维钧总说:
“每次赛跑我都到底;通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比先到终点的运动员落后好几分钟。”(顾维钧,1983:40-41)
字里行间似有几分自嘲之意。然而,功过褒贬见仁见智,毕竟,屡战屡败的记录却也恰是屡败屡战的明证。
当然,这位未来的并不总是“寸步不让”,有时,他也深谙“战略性放弃”的要诀。比如,作为船队的舵手,顾维钧就曾经“半途而废”:
“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有的划手不听指挥。教练让我骂他们。两周之后,我决定退出。我告诉教练我不会骂人。他说,任何人都能学会骂人,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我说,不行,我的英文还不足以用来骂人。就这样,我不干了。”(顾维钧,1983:40)
“我对足球也有兴趣。[…]但是有一天,球打中了我的腹部正中,我当场昏倒。我对足球的兴趣也就此结束。”(顾维钧,1983:41)
“经过两年刻苦之后,我唯一感到满意的是1910年夏中国学生会议时赢得了双打比赛。当时我在底线,我的搭档在网下。打赢这场比赛是由于他在网下的精湛球艺,而不是我在底线)哥伦比亚大学,图片来源:
在哥大,顾维钧的外交和谈判技巧已然初露端倪。当时,学校要选举九名学生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师生和学校打交道。顾维钧也参与了竞选,他的策略很简单:
但是,倘若将单纯的利益交换奉为圭臬,以为这便是顾维钧成功当选的全部法宝,那就大错特错了。更重要的是,顾维钧交友广泛,始终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对任何种族、教的人都能平等相待。他说:
“在个人的交往中,要紧的并不是他朋友的教;个性、品质和情操比更为重要。”(顾维钧,1983:44)
“在校内,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是的,同时也有很多人是其他教的。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感到他们宁可投中国人一票,也不愿意投其他那一派的人一票。这使我处于有利地位,得到了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双方的支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在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原因。”(顾维钧,1983:43)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已是百年。百年后的今天,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甚至于种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也许,当时的顾维钧并未料到,纵使逝者如斯、一去不返,他早已勘破的“团结各方、求同存异”的却仍未过时。
一个学者的能够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这固然体现了他的远瞩;然而,倘若一个外交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一个世纪以前别无二致,那恐怕也只能让人哀叹江山不幸了,因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始终都在原地踏步、裹足不前。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家。1904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于哥大获得文学学士 (B.A CC’ 1908)、学硕士 (M.A in Political Science)、国际法及外交博士 (Ph.D)学位。1912年回国后,历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中华北洋国务总理,国民驻法、英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在会上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1945年6月,出席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被誉为“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回忆录》的珍贵手稿现藏于哥大巴特勒图书馆六层的善本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6th Floor @ Butler Library)。百年之后,爱徒的著作藏于以命名的母校图书馆,想来也算是一段趣事。如果你身在哥大,又恰巧对这本书感兴趣,欢迎前去借阅。详细地址和图书编码请见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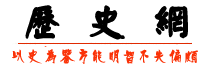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