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茶文化专家,中国农业考古的。曾创办《农业考古》。著有《论农业考古》、《中国稻作的起源》、《中国农业考古图录》、《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等著。努力促进中国茶文化复兴。并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进行“文化兴农”实践,惠泽当地百姓。
十一年前,在雅安和陈文华先生、余悦先生的合影,直到这次清明在南昌茶事活动时被陈老师整理出来发我,我才首次看到。陈老师仙逝近四年了,总感觉他就在我们中间,笑着用长长手指数点江山,一股与生俱来的羽化气象,那是真正的低调奢华,美得丰满。
陈老师的身份,真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楚。您要是看他那副架着眼镜、眉清目秀的清瘦的模样,一副高级知识范儿;要说社会地位,按照目前场面上官本位的介绍法,陈老师是前全国政协委员,前民进,江西省前社科院副院长;要说学术地位,那就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唯一的大型农业考古文化学术《农业考古》的创始人,主编,名誉主编,中国茶文化界扛鼎中人;要是想追溯他的大开大阖的个人历史,您不用说他本是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高才生,您只要说一句,他是个“老”!哇,肯定有人张大嘴巴说:不可能,陈老师看上去那么年轻,够不上那个年代吧!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文华老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1993年9月,法门寺博物馆主办了唐代茶文化学术座谈会,专题讨论法门寺唐代茶文化陈列、研究及唐代茶道的恢复等问题。那时地宫中的金质茶具出土时间不长,研究正热着呢,身为《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的主编陈文华研究员到场了。我那时虽然已经投身于茶文化,但心态是个票友,作为央视首部茶文化大型专题片《话说茶文化》的总撰稿人,为拍摄茶文化也到了法门寺现场。虽然,法门寺地宫文物已经出土,唐僖那套金银茶具已经惊艳世界。但我对法门寺的潜在热情,总体还停留在点名的那个戏剧人物《法门寺》的“贾桂”身上。“不敢坐”,这句贾桂的名言,是一提起法门寺我就会想到的那句话,对茶文化的那个茶人圈,本人还是没有太多了解的。陈老师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和茶文化无关,完全由他个人的才华呈现决定。
报到那天晚上,大雨骤然而至,第二天的露天开幕式,还能不能开呢?我们这些与会人员可想不到那么多,我只管自己能够采访到人拍摄到人就够了。后来我才听说,参与布展的工作人员,负责会议的大小官员都急坏了,总算心诚则灵啊,换来了第二天风和日丽。
开幕式由陈文华老师主持,二十年前的他,和晚年的他始终没太大变化,也是一个高挑清秀的个儿,穿着衬衣西裤,衬衣系在西裤里。他戴着一副变色眼镜,很洋气的样子,一上场那种控制全场的能力就出来了,国语虽然还带着略微的闽南腔,但洋溢,手势有力,让人想起《列宁》或者《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电影里的的。总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格,国的风格。他的言说主持,有些语句显然是即兴的,但发挥得极好,我清楚地记得,他提到了昨夜的风狂雨骤,提到了今天的云开雾散,风和日丽,提到了对我们这些茶人活动的眷顾,顿时就一阵啧啧地响应。如此一番开场白后,传来了人们由衷的掌声。这一刻我记下了这个茶人的亮相,虽然我完全没有把他和主编对上号,他那么文艺,和省社科院的副院长实在貌似挨不上。
然而,要说到我和陈老师的,真不是从以上那些料开始的。2007年3月,本人进入浙江农林大学从事专业的王学兵和范冰冰茶文化教学,狂读了一阵茶文化的教材,其中陈老师的《中国茶文化学》是我的重点读物。里面在文艺与茶的那一章里,还看到了陈老师对我小说《茶人三部曲》的介绍,知道我至少进入了陈老师的视野。进校后第一个活动就是去雅安开茶文化会议,前面提到的那张照片,就是在那时候拍的。在会上再次见到了陈老师,真是几乎一点没变,陈老师是一棵常青藤。而且以往认为陈老师私下里应是个清高寡言之人的判断十分错误。可以那么说,像陈老师那么有一颗赤子、又可以那么玉树临风的人,真是罕见,他仿佛是径直从东晋的竹林里走出来的。
我们在会流了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范畴和定义,我与陈老师可以说是高度统一,这真令人喜出望外。因为刚从作家协会转到高校和中国茶文化圈,实在还是有点忐忑的。说起来我们的这次见面也极为戏剧性,开完会我们同车离开雅安去机场,一上陈老师向我们这些晚辈拉开了话匣子,他讲他那些经历,从五十年代一直讲到九十年代,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机场到了,兴奋的陈老师一摸口袋,坏了,把身份证和机票全忘在宾馆了。因为我帮他善后处理了下,使陈老师能够正常时间登机,或许因此也留下了一点记忆,这也是后来我赶斗胆请陈老师出演我们《中国茶谣》说书人一角的底气。我想,陈老师多少会对我留下点好印象吧。
陈老师是我们的大型舞台茶文化艺术呈现《中国茶谣》的主创人员,灵魂人物。没有他,我们这台大型的茶文化艺术呈现,可真是扛不起来的呢。虽然曾经有二十年间我并没有和陈老师个人有任何来往,但这并不影响我在二十年以后邀请陈老师出演《中国茶谣》中说书人——我自以为,这个人物,非已经古稀的陈老师出演莫属。
但是陈文华先生的热烈响应还是出乎我意料。我总觉得让一个著名学者脂粉登场演个说书人,是不是太低就了,给他发信过去时很怕他反感,甚至不敢打电话说此事。没想到陈老师十分喜欢。陈夫人一再告诉我,请他出书人,是他晚年生涯的一个巨大的欣慰和人生实现,因为陈老师最早的理想就是当舞台演员,考的就是戏剧学院,可惜铩羽而归。五十年以后,他终于等来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因为他工作太忙,我们总是把他的台词抄好,贴在道具扇子上,让他方便对台词。他也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天黑才到,有一次到后让我们满大街找买治糖尿病的药,他有糖尿病,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的。
陈老师有一种本事,把非常忙碌的工作呈现得非常潇洒。他几乎每次来时都会带一大沓稿子,只有从他只会在打印或手写稿上编辑这个细节上,你才可以想到,陈老师原来的确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一叠纸稿,用麻绳绑上,潇洒地拎在手中,然后要我们买张火车票,他自己就可以去上车了。有一次我把他送到火车站,他一定要我先走,原来他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他要住下,审完稿子再自己回江西。我觉得一个老人这样一个人走实在是有点令人惆怅,他却完全不在乎,说他早就习惯这样了。
有一段时间,陈老师常来学校,参加我们的各种演出,他匆匆来去,却饶有兴致地参与排练。他每一次的演出,总是能够达到比预期更好的效果,因为他只要站在那里,就是一道亮丽的茶文化风景线。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告诉我他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建设中国第一个茶文化村,专门生产晓起皇菊,帮助乡亲脱贫致富。他说因为他做这件事情,许多人说他傻,他干脆就给自己生产的皇菊取了个品牌名:傻教授牌。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侧过头来跟我说:也许我真的做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说呢?我用十年时间,我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了,是不是?
而我呢,既对他的傻教授牌不曾理解,也对他说他用十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的问号不曾理解。首先我就认为陈老师绝顶聪明,为什么要用傻教授牌?再说在农村里做一个茶文化村,就算是中国第一茶文化村,为什么会对他那么的重要呢?我含含糊糊地响应着他的话,只是想让他高兴罢了。直到有一天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皇菊的故事。
有一次,他听说在江西婺源的上晓起村,有一台木制的水利碾茶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下放青年亲手制作的。他很是兴奋,亲自赶去现场考察。一看就喜欢上了,心想这么好的东西,要用起来啊。这样就开始在那里打造茶文化村了。他搞了农业合作社,搞了幼儿园,茶文化展示馆。但那里的农民还是很穷啊,陈老师就想到了要种什么农产品来让这里的人们致富。有一次他上了黄山,发现那里有一些白菊花长得很好,心想清茶加菊花,也是绝配嘛。于是就租了农民的地,引进了白菊花,好不容易长成了,一场大水,把一片白菊花冲得精光。
就在一片狼藉之间的高地上,有一株金的菊花,长得遒劲而有力,迎风不倒。陈老师想,不错啊,白菊花去了花来吧。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株花带回了家,种在家里阳台上的花盆里。没想到这来年开得灿烂辉煌。陈老师把这阳台上的做了种,再次撒到上晓起村的农田中。成功了!农民们纷纷引种,上晓起村从此成了菊花村,陈老师给它取了个好名字,皇菊。
我后来去了上晓起村,才明白陈老师做了什么样神圣的事情。这个村子几乎家家种皇菊,如果说在婺源春天看的是油菜花,那么深秋看的就是皇菊花啊。
2013年初夏,陈老师顺道来我们的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参与我们一个茶文化视频课程的评审。好不容易两天忙下来了,晚上,我们将进行一场茶会清谈。大家就在学院露台上。抬头看,浅蓝的天空,一弯极淡的弦月,一阵惬意的风抚过脸去,便回过神来一想,哇,今天恰好是小满啊。
茶人还是得说茶事,在我们江南,茶自清明前后摘到立夏前,那就是春茶已毕,该施肥施肥,该捕虫捕虫了。小满多雨,不过那天晚上清风明月,心情舒畅,来了一群人,有教授,有,小满的月光很美丽,大家围着陈老师,端上了用晓起皇菊冲泡的安吉白茶。
这样的夜晚,之所以喝白茶最爽,乃因为清风拂夜,向晚时分,天空浅蓝,疏月浅白,而我们这些布衣书生,白日常常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今夜难得恬淡一回,正要以淡入味。我没有想到,陈文华老师在这样的月光下,感慨万千,本来是要讲一讲茶文化的,结果诗兴大发,从遥远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说来。
陈老师是从青梅竹马开始说起的,我把它记录下来,关键词还真不少,大致如下:青梅竹马,上大学,老干部,分手,考上海戏剧学院;北师大;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好;左,右,日记,,打成,断绝关系;照片剪开;,祖国在我的怀中,你在我的心中;发配江西,博物馆;结婚找对象;;创建《农业考古》;成就“茶文化专号”;再见初恋情人;心如槁灰;傻教授;晓起皇菊;美丽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陈文华老师,年轻时便是个文艺青年,风流倜傥型的俊秀才子。1935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他,虽然有着华侨背景,但普通的农家子弟,并不曾有特殊的书香门第的家学,更无豪门子弟一掷千金的背景,他就是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文艺种子,从小就自信,健康,加上从出发看,他家庭出生好,便一顺风顺水,进入高中。
令人不解的是,本应该最讲的他,却长了一副小布尔乔亚的心肠,一套小资情调的做派:诸如散漫,诗情画意,文艺范儿,自以为是,这些毛病他那里全齐了。1954年初夏的陈文华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他的愿望是进入核心艺术圈。没想到到了上海,第一轮便被刷了下来,理由很简单,陈文华的闽南普通话不行啊。陈文华看着那坐在主考置上的也是一口闽南腔的大艺术家,心想:您的普通话还不如我的呢!
垂头丧气的陈文华回到厦门,那里有个他并不觉得好的消息等着他: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了他,这位活泼轻盈的才子,要去学习一个最古老沧桑的学问——考古学了。
正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文华在学校各个间活动,又朗诵,又作曲,又指挥,又唱歌,又写作,又读书,又劳动,算得上是一个厦大的大红人。然后,还没回过神来怎么回事,他已经成为学生了。22岁的陈文华,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到了江西,绕来绕去的,重要岗位都不能要他,最后省博物馆考古部门收留了他,也就此成全了陈文华。在无数个学习的日夜,也难免还穿插着考古、田野考察的业务活动,陈文华也总有夜宿荒野枯坟的专业经历,这些日子不让他悲凉,反让他充实。
说着说着,陈老师突然从往事中抽身过来了,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天空浅月:今天是来讲茶文化的,心情好,天气好,茶好,讲着讲着,就光讲自己了。
一杯白茶,已经续过了几次,天色已黑,星光灿烂,一群年轻茶人学者,就这样坐在学院的露台上,听一位老茶人学者叙说往事。这样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想在舞台和银幕上实现自己的年轻人,最后学了考古,并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人是到哪里也不灰心的,到哪里都要建设我们的生活的。因此,便有了“农业”加“考古”这样一个复合。1981年,《农业考古》诞生;1986年被日本考古学界誉为“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1991年《农业考古》上开办《中国茶文化专号》,开辟了茶文化研究、茶话、茶诗、茶艺、茶具、茶馆、茶场记事、茶与名人等十多个栏目,成为我国研究茶文化的权威,陈老师就这样走进了茶领域。
灿烂的花在水中绽放,小满的月光浸润着它,它像月光宝石般闪亮迷人,心都被这温柔的吸引了。
80岁的陈文华先生是在2014年5月的一天,于出差北国茶事的活动中,突然仙逝的。谁能想到,第二年小满那天,我会在厦门大学旁的大海,和陈老师的家人们一起捧撒陈老师的骨灰。想去年春天啜浅茶,白茶对菊皇。今年小满,大海长风,一缕茶魂,尽向浩空。因为陈老师说过,他走后要和大海在一起。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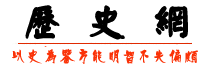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