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琾1921年冬,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先贤创刊《学衡》,翌年1月正式出版。《学衡》刊载的第一篇文章是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起草的《学衡简章》,开明提出《学衡》的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之眼光,行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此后,以《学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史称“学衡派”。
学衡派深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影响,是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一场高峰。它最早发现文明的现代性危机的人文主义学者,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提醒人们对文化应该以审慎的眼光择善而从,在今日看来,颇有先见之明。然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学衡派无疑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由于反对新文化运动,它往往被为卫式的老古董形象。1946年,学衡派的中心人物之一吴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沉痛地说道:“予半生经历,瘁于《学衡》,知我罪我,请视此书。”
2014年12月,在“学衡派”的旧地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管理学院和历史学院双聘教授孙江担任主任,致力于推动和深化概念史、学衡派、近世文化、公共记忆、民间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2016年,中心更名为学衡研究院。2016年12月22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成立二周年庆典暨《新学衡》、《记忆中的历史》新书首发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举行。
南京大学朱庆葆教授长期从事校史研究,对学衡派的历史自然再熟悉不过。朱庆葆在致辞中指出,学衡派曾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相对应的文化,以往学界往往称这股为“文化复古主义”,但这实际上是对学衡派的,它应当被视为“文化主义”。学衡派的是兼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贯通之思想,而非一味偏颇于哪一方面。学衡派是南大学术的标志性学派,当下或可称之为南京大学的“记忆之场”。
那么,今天该如何纪念学衡派呢?朱庆葆认为,学衡研究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目前,研究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在公共记忆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等方面,已成为国内学界的重镇。学衡研究院新近创立的机关刊物《新学衡》,更体现了“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并重。
朱庆葆进一步指出,继承和发扬学衡派的事业,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阐求真理”,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大学就是以学者、学生为主体构成的,以探求真理为目标的学术共同体。”因而对南京大学的学人来说,探求真理实际上就是在发扬学衡派的学术。二是“学术传统,昌明国粹”,要具有文化自信,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三是“融化新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都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的优秀资源,但这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要融化,只有在吸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之可以真正为我所用。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写道:历史就是调查研究及其结果,而过去发生的东西则被他称为事物。这与今人对历史研究的认知完全不同:历史似乎应当是过去发生的东西。而对学衡派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翻出来再看,其意义之大,值得我们深思,因而有必要重新发现与认知学衡派。
1922年2月4日,周作人化名式芬,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评尝试集匡谬》一文,胡先骕刊载在《学衡》第一期上的《评〈尝试集〉》。2月9日,鲁迅化名风声,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估“学衡”》一文,称学衡派为“实在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在周氏兄弟的两篇文章中,多尖酸刻薄之语。孙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由于周氏兄弟巨大的影响力,这两篇文章对日后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这两篇文章言辞过激,对“学衡派”追求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的目标,抱着一种嘲笑心态。翌年,一位日本记者橘朴前来拜访周氏兄弟,精通中国文化的橘朴,迫切想要知道中国的新思想家们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然而鲁迅脱口而出:“中国的事情一切都糟透了。”这使橘朴大吃一惊,不禁感慨“今天文明了世界,即使在中国,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受其而用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国家的事情”,“我认为那种态度是错误的,中国有中国的尺度”。
因此,对学衡派,我们有必要在一种“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对其文化层理进行细致地梳理。实际上,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学衡派,都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在面临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下寻求的应对之策。借用学衡派、汤用彤之子汤一介的说法:“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主义,都是中国知识为了救国进行的尝试,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因而重新阐述这段历史,显得更有意义。关于“学衡”的含义的解释有很多,而《学衡》的英文名是“Critical Review”,直译成中文即“性评论”。由此可见,它绝非纯粹保守主义,也非无条件接受,而是性思考之后对知识的接受。学衡派结合当时时代的要求,推动中国学术向前发展,留下了中国学术的尺度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学衡派的研究,放在今日,仍有价值。
那么,研究学衡派的切入口在哪呢?概念史研究或许是一个突破口。孙江介绍道,“概念史”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时代特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借用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的话,可谓之“马鞍时代”。源自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借助日本的“和制汉语”在20世纪初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社会概念。因此需要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重点是进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较研究: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语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日之间的差异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概念,不过一百多年,学科体系的固化、却早已形成,因而更需要概念史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当下,对很多基本概念,学者日用而未必尽知。学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则是通向这些基本概念研究的一条小径。该刊从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制度等入手,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最后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它同时也表明了孙江的计划:撰写影响20世纪中国及东亚历史的100个关键概念大辞典。
与此同时,孙江深感跨文化、跨学科的记忆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实记忆研究比起传统的学术分科,更容易引起学者的共鸣。他表示,今后关于记忆研究,将会着力于两个方面:理论与。“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中的《记忆之场》与《记忆中的历史》已先后出版,其他的译作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翻译中。而关于记忆的研究,学衡研究院也将陆续推出“学衡历史与记忆研究丛书”。
谈至概念史,管理学院教授张凤阳在致辞中指出,在学领域,不知道一些基本概念根本寸步难行。话语的表达方式并非是既有的,中国现在许多学术概念实际上都源于,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因而亟需关注来自的概念最后如何嵌入我们今日的知识结构中。概念史研究借鉴了知识考古的方法,以此来考察东亚知识系统如何摆脱传统从而获得了现代性。在哲学研究中,选择和确定典型范本的时候,会把目光聚焦于所谓的“成熟形态”。但在史学家那里,“知识考古”的兴趣也许会优先指向某些概念在话语变迁过程中的初始表达或萌芽形式。因此,如果关注的是同一个基本概念,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在思维流程上似乎是相反的,这使得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
那么,如何建设中国的话语体系呢?张凤阳说,今日中国需要“新青年”式的,因为当今中国社会有许多公共议题需要学者进行讨论,同时也应继承学衡派“论究学术”的,深入发掘真正的学术。他认为,应该做两种学问——锦上添花式的学问和雪中送炭式的学问。身为学者,面对社会公共议题,要着意于所探讨公共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但针对那些相对冷僻,在知识累进过程中重要的问题则更要加以关注。而概念、梳理概念的过程即是此类,做踏实的学术工作,这也是学衡派的研究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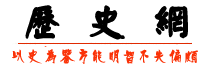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