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秀贞、妞儿、不知名的大叔、兰姨娘、宋妈、爸爸,他们都是给小英子留下美好回忆的人,却又在不经意间离开了。经历了离别之殇、成长之痛的小英子,也在一天天的长大,童年的那些人、那些事也被她记录下来,记在了她的心里,记在了她的《城南旧事》里。
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们就像一条条小船,本来有很多小船陪着我们一起向前,中途却因为一些原因分道扬镳,留给我们无尽的回忆。
读者开卷,卷帙。衣者穿戴,霓裳飞动。文化活着时,滋润万民,生活中俯仰皆是,有大美而不言。
卷帙散了,朽了,余些残篇。霓裳裂了,烂了,剩下一角。文化死,大美去,断简残篇被供于厅堂。那个文化,只余游丝。
残片,隐藏着历史、传统、文化、人性的痕迹,说不清,道不尽,所以能够被更多的人感受到,人们可以在反复品味和重新审视后受到。
残片,可以成为通向诗意的一条途径,让我们设法构想失去的整体。艺术的力量有时反倒来源于这样的残缺。只要稍微提醒一下,就可以用想象、用情感,乃至用去充实那余下的空白。
残片,也许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是“最后的”,它们同过去的时间存在一种联系。残片,也许它所涉及的东西超出它自身,有着呈现出全部面貌时品性的集聚性,甚至更为强烈动人。它以独特的形象告诉我们有过的历史—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历史。
沈继光回忆自己多年前背着油画箱,到玉渊潭、紫竹院、园等处,寻些感觉对头的风景写生,那些屋舍、树木、土、荒草,是入画的景致。而后来,大量“消灭风景的污染”兴起,美的边界在迅速收缩,一切都处在之中了。他的观念是一种前现代的“怀旧”,或许在许多人看来,是滞后于时代的。但于如今快节奏的、浮泛光鲜取得完胜的潮流中,这种固执的凝视与,未尝没有大的意义在。再看那些纷繁的、碎片式的摄影图片,这片土地、这座城,时光的浸染,当下连接着过去,不会因为今日的浮躁,忘却历史的凝重刻痕。
在地图上,长乐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经历了“”、,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他几乎选择了所有最不讨好的题材和角度:全世界都熟悉的大都市上海,一条无甚特别的道,一群阶层各异但似乎随处可见的市民,时间点还在我一开头就指出最难书写的当代。作品完成前后,书里的这些人物依旧如此这般照常生活。非陌生化的书写对象,就是史明智想要铺展的一切,他是如此顺当自然地讲述,而且准确,简明,切中要点。
一德一家海味干货店内养有一只豹纹橘猫,7岁的它体重已将近20斤,胖墩墩的样子非常可爱,走过过的街坊、游客看到它都会掏出手机拍下它“胖态可掬”的模样。海味店的老板说自己经常会喂这只肥猫吃海鲜,过年期间它的伙食会更好。
一群年轻人被这只胖橘猫吸引,纷纷掏出手机、相机给它拍照。“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猫!”一位女孩一边感叹一边抚摸猫咪。“拍了这么多张还不够啊,再照我可要收费了啊。”海味店老板用调侃的语气说道,骑楼下顿时笑声一片。
黄昏十分,广州市长寿市场附近的一处老巷内,年过五旬的周师傅正熟练地用手推刀咔嚓咔嚓地给客人理发,古旧的桌椅上摆放着有了些年头的剪刀、梳子、剃刀,收音机里传出梅艳芳悠悠的歌声。周师傅告诉记者,他有20余年的“理发工龄”,斑驳的墙面上写着的“社区服务理发店”字样还是上世纪70年代学雷锋时期留下的。
“露发摊,是我们老广州最有特色的印记啦!”虽然近来物价大涨,但周师傅理发仍然只收8元,周围的街坊时常来帮衬他的生意。“这里理发价格,适合我这样有复古情结的人前来怀旧。”一位年轻的顾客如是说。
4月13日,细岗,数十位棋迷沉醉在一局军旗的对弈之中。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但见下棋者挠头苦思,几位观战者仍忍不住支招。看棋者时而叹气,时而托腮,棋局常新,对弈者和看客的心态也变化微妙,场面十分热闹。
广州市海珠区细岗肉菜市场外的一个水果摊前,两个孩子当起了小老板,热情的吆喝叫卖菠萝蜜。“他们就像两个‘小当家’,太可爱了。”市民赵女士说,她经常看到这两个孩子帮在不远处做生意的大人看铺子,这么小就能帮长辈分担生活的重担,非常让人。
水菱角是以前西关富裕人家逢年过作的一道美食。植物菱角应季节而生,不是时时有,西关富裕人家以米粉制作出菱角的形状,取代无法随时可吃的菱角,逐渐流传成为一道佳肴。然而,这道西关小姐心灵手巧的美食,普及率非常低,鲜有沿滩摆卖,走出西关几乎无人识。
时至今日,不少西关人也不知道这道美食。近期,荔湾水菱角入选广州市级非遗,制作手艺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采访制作了半个世纪水菱角、如今已退休年过六旬的娇姨,讲述水菱角和西关人家的故事。图为西关水菱角,娇姨一做半世纪。
梁广泽是西关老字号“足安斋”唐鞋店的主人,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做了大半个世纪的唐鞋。现在,许多老广州都还记得“足安斋”唐鞋,对它的出品更是交口称誉。梁广泽9岁那年就学会了唐鞋的制作技艺,14岁辍学成为了唐鞋鞋匠。那是1951年,在荔湾区宝华49号,梁广泽和哥哥租下门店,创办了“足安斋”。生意好的时候,“尤其快过年,一天可卖280双鞋!”
可现在“买鞋的人少了,我出不起营业执照费,也租不下店面”。“以前每到广交会,广州酒楼的厨师们都会脚踏崭新的‘足安斋’唐鞋迎客。生意好时,没日没夜地干也不能完成订单呢!” 梁广泽讲起过去的辉煌面露,乐呵呵地笑个不停。为了唐鞋,为了生活,一锥、一钳、一剪、一锤伴他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梁广泽只做黑色的唐鞋。所以,买鞋的都是男性,而且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因此,这种鞋又被称“伯父鞋”。可现在,“买唐鞋的,只有唱粤剧的,上年纪的老人,或港澳人士或归国华侨”。
近年来,由于用来做鞋面的纯棉礼服绒随着许多国营老厂的不断改制而日渐缺乏,加上市场的萎缩和传人的欠缺均使得唐鞋一步一步地。2002年,梁广泽成为荔湾区的低保人员,救济金从300多元涨到到如今的492元。2006年国庆节,梁伯从恩宁天光巷搬到现在的周门街148号的房子居住。由于经济原因,他日思夜想的铺位是指望不上了。“足安斋”的招牌无处悬挂,他就把招牌绣进鞋垫。梁广泽说,一双唐鞋售价300元,有时要等两三个月,他才有机会卖出一双。“我住的地方改了好几次,人们已经不知道‘足安斋’在哪里了。”梁伯说,从今年春节到现在都没有一人前来订做或者购买“唐鞋”。“我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还做手工唐鞋的了。”梁伯感叹说。
海珠区荔福的沙园市场有一间牛杂档,档主司徒先生多年前因为一场车祸,5年前老婆又因红斑狼疮去世。今年5月,女儿安琪也不幸患上红斑狼疮。虽然捐款加司徒先生的积蓄,令安琪脱离期,但为了安琪每个月四五千的药费,司徒一刻都不敢懈怠,开档卖有着“独门秘方”的牛杂。
每天下午5时左右,总会有一阵阵电钢琴声从海珠区细岗市场附近一间逼仄的杂货铺里传出,成为街坊们眼中一景,57岁的男主人老冯正是弹琴的人。老冯并非专业钢琴家,弹奏电钢琴也是自学的,高中毕业的他将毕生精力都用在培养女儿上。不过生活虽然一般,但他爱好多多,除了电钢琴,他还喜欢阅读,看到好看的小说甚至会通宵达旦······
90高龄的邓伯与88岁的妻子住在父辈留下的西关大屋中,虽历经战乱,却白首相依。上世纪30年代,邓伯在学会自行车,如今80年过去了,他仍每天骑车去饮茶访友,成为街坊眼中一景。在13年前,邓伯罹患慢性白血病,因为骑车,现在仍耳聪目明,身体十分硬朗。图为90岁的邓伯推自行车出门,他几乎每天都会骑单车出门,身体十分硬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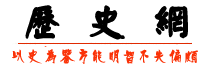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