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爲据点,但这并不是单单爲人的行动计划。在地理上被称作东亚的领域,从中国南海到海峡,从东海、黄海到日本海,都好像漂浮的“水草”,所以如此命名。
似“水草”般无所依凭的弱小力量=身体的表现,这一地区近代的历史性是如何与现在的区域学碰撞、斗争,又是怎样介入的。且把它当作,但,这正是“剧场”所憧憬的。
将这世界比喻作一匹阵痛的兽,是「海笔子帐篷剧」最近的创举。当然,对于创举的发生与否,通常并不是编导樱井大造关切或在乎的状态。应该说,埋藏在每一个戏剧更迭的瞬间里,总有一则反讽或暗喻现实的场景,将作为观众的我们,带进一处般的旷野里,展开对于现实背后所存在的思想的追索。这在他的话语里,便是「帐篷是比外在社会的现实更为现实的《场》」。这样的说法其来有自,因为帐篷与戏剧的相互连结,在一出现时,便不是为了制造美学的空间而来的;相反的,它时刻都在另立想象的,并弱小者在这里共创的现实。
围绕这齣戏的,其实是与当代世界息息相关的探索。这探索也和《场》这个实体关系密切。《场》指的自然是帐篷剧发生的场域。但,重要的是,《场》并不等于空间。因为单就空间而言,没有时间的存在是无所谓也不妨碍的;就《场》而言,则必须是:在空间中交错着时间的流动。就好比每一回的帐篷剧都存在着象征性的时空,这一次的演出将时空的主轴朝向「未来记忆」,其实便也是我们习之为常,并已多多少少感到,最终难免将会是一场豪华的美好想象——文明。
文明是怎样的一种诱因,让我们都已投入其中,而引以为豪!?是以「文明的冲突」作为一种利刃式的分野,将「文明」与「」一刀切割。让第三世界推离于第一世界中,进而举出依赖性发展的进程。在这里,性别、族群、生态问题表面上都是后现代社会中,个别去霸权核心的议题,实质上却存在着阶级结构的重要界面。一直要等到近代资本化危机出现时,当人们发现原本一直处于「少数」的弱小者,等于是这世界的「多数」时,噩梦突而掀开了热锅的压力盖,文明成了一场随时会爆裂的,一如表面光鲜却危机重重的压力锅。
这便是世界变成一匹阵痛的兽后,文明以现代化的脚色现身时,我们所亲临的世界。这齣戏中,这样的世界以「世界宫」的场域和我们谋了面。戴着长鼻子道具的时薪奴隶,揭露阶级分化已然细分到个人水平的事实。这让底层翻身的道,形成愈来愈形狭窄的境况,最后仅能被淹覆在零碎化的一滩死水中。就樱井大造的说法,经济奇迹转为剧中的「经济妖怪」;而被排挤的贫民区,在这妖怪腹中的,则是比现实更现实的现实。所以剧中的野牛,以真实中发生在的一把火所导致的「清退」事件,诉说底层思索的肌肤经历。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在某个地方落脚,和某个地方的某些人,一起建立村落。」当然,他就是帐篷时空下,想象力避难所里生产出来的人物。再者,城乡一体化,通常作为资本发展出现后遗症时,国家返身回来处理乡村凋敝、城市挤爆危机的手段。然则,眼下望去,对于后发达国度而言,这变成着讽谕的一种说法。因为,现实永远还是城乡矛盾的无决,这是剧中脚色鲲鹏遇上青鸟时,后方天窗据说即是通往太空的机场,而前方已是无国度高地Zomia 的时空对辩下,永远难以落实在答案中的失落与追索!
这自然再次提醒了观众,如何从交叠的视线去思索:不断辩证,所得来的结果。第一种可能是「无」;另一种,则是不在一个固化的立场,扮演启蒙的脚色,说出正确的语言;当然,还有的便是:帐篷剧中始终立足的流民观点——「弱小的力量,能让身边的人变身。」
「记忆徘徊在过去寂寞的,也蜷缩在未来的荒地里」,剧中的人物抛出了这样的诗句。整齣戏从一般的过去记忆,延伸到被发明出来的未来记忆。当然不仅仅是文字迷宫的转换游戏,而是如何去重新看待:当未来也形成一种记忆时,我们将如何对待这样的记忆。因为,记忆一旦留在人的身体里,便不再是身外之物,且将通过个体共同体的现身,称之为共同记忆。如是,处在当下的世界,这称作「未来记忆」的流体,换作一般的明天来看待的话,我们将继续处于惯性状态下,仰望希望到来吗? 这是文明带来危机之际,本剧抛出的另一命题。
鲁迅在散文诗〈希望〉中的名言:「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认真地看,这就是世界这匹阵痛中的兽所处的状态。就如鲁迅行文中所言,虚妄处在不明不暗中,就算寻不着身外的青春,想一掷身中的迟暮,也径自看不见前方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处在天地不着的「虚妄」下的人物,将在剧中说出:「道的道,就是人提着首级迈开来,才走出的」。因为「道」的部首就是行走的意思。亦即,提着首级行走在苍茫的虚妄中,希望一如,都不是身边得以触及的明天。这便是当下我们身处的「未来记忆」。
帐蓬剧通常都以歌唱,来做某种共同的,在某一个场合中,樱井说:「歌唱是为了解除武装。不仅解除自己们的武装,对彼此敌对的那一方也能发挥作用。唱歌能让我们返回各自的记忆。」这让我们理解到,「记忆」虽然是私有的,但基本上都是围绕集团的某些场景。也就是说,记忆是「朝向他者的记忆」。这在本剧中,也发挥着相同的功效。但是,这回演出中最后合唱出现前,观众感受到不如以往的撞击。这当然与演出场地不方便点燃火线,又或者演出原就没这样的安排有关。然则,关键的重点,应该落在两位场上人物,在最后对话时,以较为接地气的话语,为逆光中追寻着共同身影的人物与情境,画下了一个叙事性的句号。说是:「留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创造广场。把世界宫变作广场。然后,广场就要出发。」
作为长久以来,不断以建构下一次新生的帐篷剧而言,这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句号。但,详细考察这十多年来,帐篷剧在东亚的行动轨迹,却也能够相信,追寻一种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出发再起的弱小者力量,已然成为东亚/帐篷共同行动的共识。这让人想起马克斯在〈易 波纳帕的雾月18〉中所写的:当把敌人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而当再却至无可退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如果用马克思这样的观点,来作为本剧结束前的驱动全体的合唱的动能,相信得以找到某种身体在广场上出发的想象吧!
所谓的「世界」在古印度语中叫做「loka-dhaatu」,意思是「森林之中没有树的空地」。那里不但是人们聚集的场所,同时也是「传达的地方」。古代中国的佛教将这个词翻译成「世界」。意味着空间的「界」和意味着时间的「世」。「世」指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界」则是人们在这三世之间的空间。因此,所谓「世界」这个词,相较于我们一般使用的意义(万国、社会、地球等),是一个将重心放在时间上的词。
这次的剧名《世界是一匹阵痛的兽》里的「世界」,也是设定成像这样将重心放在时间上的时空。但是,它距离还很遥远,未完的过去、迟迟不到的未来、止步不前的现在,这三股力量互相角力的场域就是我们的「世界」。它的姿态是一只在夜晚为阵痛的苦楚而翻滚挣扎的兽,但是,面对这样的姿态,一味地感到恐惧是不行的。能够看顾这只兽的是身为这个「世界」当事人的我们,而且,说不定兽分娩生下的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所的(或者说居住于内部的)「兽」,看起来似乎是所谓的「文明」——象是即将崩毁的大楼一般布满裂痕的「文明」。「文明」不过是以「国家」这个社会体制做为地基的「文化」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罢了。若将「文明」的基础单纯化,看起来似乎可分成三点:第一个是阶级的分化,第二个是劳动的分工制,第三个则是都市这个场域的存在。这个「文明」正在逐渐龟裂崩毁的是:
第一,阶级分化已经细分到了个人水平(也就是说,越往下层走,安定化的阶级被切割的越加);第二,被分工的劳动价值变成一面倒地倾向消费而非倾向生产(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劳动变成均一水平,只有经济速度被奉为神明并且赋予价值);第三,都市逐渐失去「人们生活的场域」这样的场所性(也就是说,许多都市居民只能把相似于机场候机室或高速公上的车子之类的「非-场所」当成住处)。
这个「文明」的崩坏期应该是长期的吧。它以一副彷彿承受激烈阵痛的巨兽姿态,在我们的「三世」之中。那是缓缓倒下的海怪利维坦(国家)的身影?还是已然倒下并且流民化的劳动者们,彼此挤压重叠后出现的怪兽?答案无法说分明。无论如何,我们是不可能从「文明」的崩落过程中逃脱的。这么一来,除了重新理解掌握我们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并且将「生的过程」当成「文化」重新发明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的「帐篷场域」,就是其中一个像这样的小小发明现场。
特别感谢:空总文化实验室、大湾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高雄县眷村文化发展协会、差事剧团、半咖啡、小地方SEAMS、布夏拉提、流民栈、小小书房、永胜帆布、佑祥瓷器、海马回光画馆、暖暖蛇咖啡、能盛兴工厂、共艺术合作社、铁支边创作体、人咖啡、三余书店、塩旅社、绝对空间、剧场、回游式、反南铁东移全线自救联合会、反西港外环道不当开辟自救会
协力:王子豪、王信义、王思靓、王墨林、白永馨、吴永毅、吕孟恂、卓淑惠、林祐丞、林宜蓉、段惠民、徐饱、柯德峰、柯永谦、秦·KANOKO、高琇慧、许法、许斌、郭孟宽、陈乃华、陈小桦、陈香伶、陈惠善、黄涵、黄馨玉、温思妮、杨美英、杨凯婷、远藤弘贵、刘耘、郑捷任、卢崇玮、锺乔、韩恺真、蓝贝芝、龚卓军、Fri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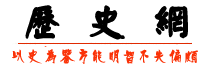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