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其实令秧是想要的,但是她的方式不是说我想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者。”上周末,青年作家笛安携新书《南方有令秧》来到“时代国际单位·南都艺术沙龙”,并以《萧红与令秧的黄金时代》为题,与观众分享新书感受。活动结束后,笛安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中,笛安就个人写作转型等话题作出回应。她说,最近一两年,自己一直想要尝试写一个当代背景下真正的罪案题材小说,但不太敢动手。“现在至少《令秧》写完,我觉得就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时候。”
原标题:笛安:读者若有刹那相信“明朝就是如此”,我就成功了
导读:有时候,我想表达“谁都没错”。我觉得,令秧这个人物身上有“气”的地方。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她其实是想要的,但是她的方式不是说我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此。就是说这个人,她可能利用、这个制度,然后在这个制度里获取的利益。有一点反讽,但我觉得就是这样。
作家笛安
“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其实令秧是想要的,但是她的方式不是说我想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者。”上周末,青年作家笛安携新书《南方有令秧》来到“时代国际单位南都艺术沙龙”,并以《萧红与令秧的黄金时代》为题,与观众分享新书感受。活动结束后,笛安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中,笛安就个人写作转型等话题作出回应。她说,最近一两年,自己一直想要尝试写一个当代背景下真正的罪案题材小说,但不太敢动手。“现在至少《令秧》写完,我觉得就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时候。”
写作转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首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没有写熟悉的青春经验。是对原来青春经验厌倦了?
笛安:不太好说,我觉得不一定以后真的再也不写少年人,或者以年轻人做主角的小说,也许还是会的。这次想写历史题材,是因为突然间觉得这个点子特别吸引我,然后我就想,至少我从来没写过、没尝试过。我还挺想挑战一次试试看,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实际上也没有说刻意地就要转型了。
南都:刚好这个故事特别吸引你?
笛安:那其实是我十年前听到的故事。但我就觉得,突然有一天,三年前的这个时候,那个为了贞节牌坊奋斗终生姑娘的形象突然间这样子闯进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妙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她身上是有反差的,她与她所处的时代之间,个人与制度之间,就是这种张力。
南都:关于新书,你曾说“真正的在于运用所有这些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要在跟我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逻辑里虚构出人物们的困境。”
笛安:我就举最具体的例子。你想写一个古人,要给人物间制造情境,以及在这个情境里发生的冲突,这些东西要用你习得的背景知识去想象,而不是用你生活中的经验,你的经验其实也用不上。例如你写现代题材的时候,你不能让男女主角,如果要谈恋爱等等,你不能让他们在行驶的飞机上发微信,这个是一个硬伤的错误。但是背景挪到古代,其实这种错误很难说你不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故事的冲突,你得确保在当年的背景里,它能合理。要运用它去构筑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去构筑这个故事,这是真正的难点。
个体与制度
南都:上你也说,《南方有令秧》是想尝试探讨人与制度的关系。此前你也在法国念到社会学硕士毕业,能不能就这本书,谈谈你想说的东西?
笛安:有时候,我想表达“谁都没错”。我觉得,令秧这个人物身上有“气”的地方。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她其实是想要的,但是她的方式不是说我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此。就是说这个人,她可能利用、这个制度,然后在这个制度里获取的利益。有一点反讽,但我觉得就是这样。
南都:书的后记中,你对自己曾经的创作模式和现在的进行比较。从局限于“表达”,到意识到写小说有远比“表达”更重要的任务。你怎么看待自己这样写作状态的变化?
笛安:这个我想可能就跟人生的体会有关系,肯定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时间会帮你改变你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我觉得人的世界观是会进化的吧。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个进化,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成为一个,隔十年二十年,自己世界观会进化一下的这么一个人。
南都:新书算作一次升级吗?
笛安: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要过一些年再看。
南都:你的写作历程还是比较顺畅。不少人赞许你比其他80后作家超人一步。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褒?
笛:谢谢(笑)。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肯定不是说跟任何人去比,我也不想和其他人去比。我觉得最关键是同过去的自己比,我需要进步,或者说需要更成熟也好,进步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希望在自己的道不停地往前走。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体育比赛,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新书遗憾
南都:写作这块,你认为自己有哪些不足?
笛安:好多呀!但是不是说,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我自己也蛮希望。就《南方有令秧》这部小说来说,其实我希望能写得更丰厚。女主角是一生没什么机会出门,所以这部小说基本上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宅院里面。但原先,我本来想这个男主角,他是可以出门的。当故事以男主角这样的一个视角在移动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把宅院外面的世界写得很丰富。但这一方面是工作量大,另外一个是我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这样写,小说的篇幅就长了,可能会更厚。我也不知道出版社对此会不会有意见。但是如果能这样写的话,外边的世界能很丰富,我觉得这个文本就更会有它的意义,就更万历年间。
南都:你说过,好的历史小说是要重建古人的价值观,要让现代人相信古人就是这样?
笛安:我记得当时在看莫言《檀香刑》的时候,就觉得他写得特别精彩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县令。他做每一件事,内心就想“你看,我就是为了百姓”。莫言创造的这个形象至少让我相信,就曾经的那个年代,这种士大夫文化体系里的人中,的确有像他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也许你觉得这个县令很可笑,但是你觉得他可信。其实《檀香刑》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其中很多背景资料都是莫言自己编的,但是至少莫言做到了。他让人相信,那时候的人,真的就是他所创造的那样。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到让一些读者看令秧的时候,一刹那间相信明朝的人就是那样的,那我就觉得自己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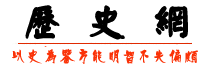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