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柴刀离树枝堪堪只剩一寸之距,白小九又再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顿足回身,四下里悄无人迹,野风拂过丛生的荒草发出沙沙声响,草叶纷纷伏低一览无余,应该不是什么人躲在附近和他开玩笑。
夜幕,一盏油灯发着昏黄微弱的,玉雪可爱的孩童正倚在床边,借着光亮缓缓翻动那本年代久远的破旧书卷。
“义父,今天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很奇怪,声音里似乎含着一种,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悲伤……义父,你留给白小九的书,我已看了很多遍,但却始终参不透您想要白小九明白的道理,书中的那位刀神玉千胜,与我又有怎样的...
手中柴刀离树枝堪堪只剩一寸之距,白小九又再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顿足回身,四下里悄无人迹,野风拂过丛生的荒草发出沙沙声响,草叶纷纷伏低一览无余,应该不是什么人躲在附近和他开玩笑。
夜幕,一盏油灯发着昏黄微弱的,玉雪可爱的孩童正倚在床边,借着光亮缓缓翻动那本年代久远的破旧书卷。
“义父,今天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很奇怪,声音里似乎含着一种,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悲伤……义父,你留给白小九的书,我已看了很多遍,但却始终参不透您想要白小九明白的道理,书中的那位刀神玉千胜,与我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白小九在灯下细细翻着记载刀神生平的书,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出白九给他留下的答案,不知不觉倦意上涌。梦中似乎隐隐有一团柔和白光,飘浮不定,忽远忽近。
白小九发现,江湖中人无论有头有脸还是默默无闻,似乎都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别号,他决定入乡随俗,也当是用新的名字来一段新的人生。所以当小酒馆里那位热情的青年拉他做介绍时,白小九想到了书中的那片竹林,说:“在下白衣沽酒,绮罗生。”
热情青年名叫一留衣,他晃了晃手中的酒瓶,笑着说:“我有故事也有酒,绮罗生,你坐下来喝一杯酒,听我讲个故事,那我们就是兄弟了。”
一留衣声情并茂地讲了个关于创业艰辛的故事,末了说既然你想练刀,不如跟我一起回去叫唤渊薮吧,人多也好有个伴。哦,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六个人,不过加上你,就是七个人,可以组成武道七修了!要不要考虑一下?”
绮罗生不太会别人,晕晕乎乎地就被拐进了七修。等安定下来,发现虽然艰苦了一些,们倒还都不错,索性将这一切看做是安排,或许自己刀道的第一步就应是如此吧。
绮罗生确实有练刀的天赋,用村里豆腐西施的话来说,那就是拎刀劈个柴火都自带武学师的潇洒大气。
看过七修刀谱的当天,绮罗生就陷入了某种近乎怀疑的沉思,一留衣只当他是初看这些东西感到新奇不解,嘱咐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来找师兄们后就消失得不见人影。绮罗生捧着刀谱研究了半天,仍觉其中错漏百出,便不再去想,睡前照例翻阅了一遍刀神轶事,掩好放在枕边。
低沉的声音回响在耳边,绮罗生隐隐觉得这时自己应该回应什么,张口却哑然失声,半晌,稳稳握刀指向那团影影绰绰的光晕,眉眼聚起凛冽之色。
绮罗生一度觉得从前自己有过一段奇遇,时至今日,那种留恋又惋惜的感觉还残留心底,却已记不清当初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了。
一留衣端着饭碗猜测他刚上叫唤渊薮水土不服才做噩梦,并就为什么要住得这么高表达了一番强烈,当场被众人赶下饭桌,吊在悬崖上好好感受来自高空的冰冽冬风。
时间总是匆匆易逝,不久后绮罗生刀道大成,决定下山去。践行宴办得不算隆重,贵在心意,酒过三巡几个人都摆手表示不行了脚底打飘,各自散去,独剩下两个酒鬼把酒言欢。
喝多了一留衣就开始打听他的感情问题,意思如今你也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考虑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啊?问只是随便问问,毕竟在苦境年龄四位数往上的单身贵族满地跑,连一留衣自己的年龄也很莫测,绮罗生在他们之间最多只能算个小娃娃。
话没说完被一阵哈哈哈哈加长版笑声打断,一留衣抱着酒瓶子无法控制地滚到桌底下,断断续续地道:“哈哈哈哈……怎么着……你还想找个……哈哈哈……找个小仙女儿啊?”
江湖往往会教给那些想要挑战它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道理,很多事情都是难以预料,更加无法掌控的。江海沉浮,身不由己。
雾气弥漫堤岸,清辉散入与黑夜融为一色的江水,绮罗生坐在船舱中自己,为什么要带上这人一起回月之画舫。本是离别前感怀的一夜,旁边毛茸茸的狗头却总在悉悉索索地搞小动作,一会儿凑过来闻他说好香,一会儿又问要摇船吗,气氛被得荡然。
北狗终于安静了下来,倚在栏边看泛白的浪尖在一片墨色中沉浮,不断被推到甲板上来撞成细碎晶莹的泡沫,看着看着,忽然若有所思地沉吟一声。
北狗从背后摸出了一本书,一阵骤来的风哗啦啦吹乱书页,露出已有些斑驳的字迹。“原来就是它方才一直硌着我,嗯,找到了。”
清徐的风伴着缓缓吟诵声,绮罗生闭眼,儿时曾读过无数次的内容,此时再由旁人口中念出竟会有种别样的感受。正自内心触动,声音却忽然止住,不由道:“怎不继续念下去了?”
“书中所写的内容,让吾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熟悉,好像曾经见过,又好像亲自感受过。绮罗生,这书你从何处得来?”
北狗哦了一声,说不上失望还是不在意,绮罗生再想问时,却见他环着双臂微微低头,狗头帽罩住了大半张脸,细小绒毛随着呼吸拂动,显是已睡着了。
这是他宿在玉阳江上的最后一个夜晚了,明天开始,他就要依照约定代替北狗进入时间城,迎接又一个未知的全新命运。
飘浮于悠悠云海之上,时间城如同清静的世外仙境,终日只闻时针规律转动的清脆滴答,地广人稀,不染凡尘。尽管北狗曾言时间城中住着许多人,需要才能遇到,绮罗生还是觉得这城中未免缺了点烟火气。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紫火王和随遇来到时间城才有些好转,城主对活泼的小紫火尤其喜爱,除了喝茶吃点心和饮岁拌嘴,最大的乐趣就是逗弄这个孩子。不必于时间树下聆听片片光阴流逝的时候,绮罗生也会来到翡冷翠花园中,与他们一同玩乐。
这一天,绮罗生奉城主之命到城中的藏书室找几本儿童读物,仔细挑选后正欲离去之际,不知是否巧合,一本书从高高堆摞的书架上掉落下来,恰巧落入他的怀中。
绮罗生伸手摩挲着光洁如新的书皮封面,略一沉吟,道:“这与吾义父留下的刀神传所写内容分毫不差,难道说是城主您有意安排?那么,吾父白九又是……”
“白九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樵夫,你不用多想。”城主移步转身,一手轻轻背在身后,“至于吾为何要这么做,哈,聪明如绮罗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北狗哼了一声扭头,手却抓着他的袖子:“你倒会享受。哼,城主就是故意要留你,吾每日辛劳奔波为苦境做事,回来却连见你一面都难。”
这话明显地带了些别的意思,绮罗生微微垂眼,不知他有心或无意,合扇轻轻敲了下北狗手背:“好啦,莫乱发脾气。”
北狗扯着绮罗生到时间树下坐,小蜜桃摇了摇尾巴他俩挪出空地,过了一会,在北狗眼神示意下不情不愿起身,一步一摇地走远了。
那一天,阳光正好,鸟雀欢鸣。全城的人都涌至时间天池边为晷士和他的爱人送上祝福,共同这令人喜悦的一刻。
场面十分轰动,小紫火和随遇在满地鲜花里绕场乱跑,城主一面安抚群众一面发表致辞,饮岁站在旁边,深受感染,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掏出了手帕擦眼泪。
颜面神经失调的最光阴一语不发,忽然觉得掌心被捏了下,转头,绮罗生唇角含着浅浅的笑意,好像正要靠过来和他说点什么。他的眼睛里有最温柔璀璨的星光,最光阴想。
到了晚上,绮罗生正在房间里翻看着城主送来的礼物,忽然背后一人俯下来拥住他,亲亲鬓角蹭蹭脸颊,像只狗儿黏着人撒娇。
被爱人拥在怀里珍惜对待,绮罗生满腔柔情,心意忽动,翻到最后一页手指轻轻一点,侧头看向最光阴:“如今一切皆已落下帷幕,这本记载着九千胜与最光阴故事的书,是否也该有个结局了?”
最光阴便明白了,轻轻嗯了一声,伸手覆上绮罗生的手,与他一起在书的末尾落白处,一笔一画地写道。
今天的活动,赶个末班车。π_π感觉画这种东西真是吃力不讨好,自己也做不到尽力,因为不停的狂躁→_→
今天的活动,赶个末班车。π_π感觉画这种东西真是吃力不讨好,自己也做不到尽力,因为不停的狂躁→_→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事儿年龄不到确实看不明白,阅历不足,也不会有那么深沉的累积,文字自然就看着浅薄又吃力。我试图写深刻的东西,却明显感到了力不从心,笔力不足以驾驭那么大的内容,就只能存一个一个的脑洞,等待未来某一天能挖出来。可是这过程中还有多少丢失,就不得知。
我尝试突破年龄的,可是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自己还是处于写风花雪月,或者一个人的小江湖的时期。一遍又一遍下笔,一遍又一遍让自己失望,可能这就是边界。
不知道自己还能多久,真的怕自己年龄到了,却没有心情和心力,不能再拿笔,思维枯竭江郎才尽。
有些事儿年龄不到确实看不明白,阅历不足,也不会有那么深沉的累积,文字自然就看着浅薄又吃力。我试图写深刻的东西,却明显感到了力不从心,笔力不足以驾驭那么大的内容,就只能存一个一个的脑洞,等待未来某一天能挖出来。可是这过程中还有多少丢失,就不得知。
我尝试突破年龄的,可是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自己还是处于写风花雪月,或者一个人的小江湖的时期。一遍又一遍下笔,一遍又一遍让自己失望,可能这就是边界。
不知道自己还能多久,真的怕自己年龄到了,却没有心情和心力,不能再拿笔,思维枯竭江郎才尽。
宋青州抬起头,所见便是一座斗大的碑帖,开阖之间颇具柳骨颜筋。顶端高坐一人,衣衫半敞,手里攥着只五色笔,斜撑攲枕,颇有种魏晋气度。
宋青州是识得他的,或者说鲜少有江湖人不识得他。青岩江辞,长于百花拂穴手,又人如其名,天生一段峻瘦风骨。
见他来了,江辞旋即便抚掌而笑,扶摇直下,走近宋青州身旁,手腕一挑,五色笔顺势挑上宋青州鬓边一绺,惹得宋青州颇不自在。没奈何,宋青州似笑非笑与他一眼,反手握住他笔杆三寸。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江辞同宋青州大抵有三年未见,一个于华山清修悟道,论剑峰顶吹了三年的冷风;一个背着药箧,游尽十四...
宋青州抬起头,所见便是一座斗大的碑帖,开阖之间颇具柳骨颜筋。顶端高坐一人,衣衫半敞,手里攥着只五色笔,斜撑攲枕,颇有种魏晋气度。
宋青州是识得他的,或者说鲜少有江湖人不识得他。青岩江辞,长于百花拂穴手,又人如其名,天生一段峻瘦风骨。
见他来了,江辞旋即便抚掌而笑,扶摇直下,走近宋青州身旁,手腕一挑,五色笔顺势挑上宋青州鬓边一绺,惹得宋青州颇不自在。没奈何,宋青州似笑非笑与他一眼,反手握住他笔杆三寸。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江辞同宋青州大抵有三年未见,一个于华山清修悟道,论剑峰顶吹了三年的冷风;一个背着药箧,游尽十四州。期间虽有鸿雁传书,到底难现音容。
约莫是丙子年年末,江辞实在想宋青州想得紧了,顾不得甚么,揣着药铺里的盘缠就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将近三个月的日日夜夜,划破洞庭山水,走过凌烟夕阳,他自白茫茫一片天地的年节走来,欲往桃李春风一杯酒的暮春而去。
他掀开帘招,大马金刀地坐在车架上,单手把着车轼,抬眼望着华山的方向。沿上多碰见相熟的友人,友人问他:“你往何处去?”
空濛的山色因烟雨更青,落在官道上行人眼底,就成了文人笔下“苍翠欲滴”四个字。待到江辞终于抵达华山时,已然从佳瑞时节到了夏始春余。
江辞记着他下青岩时,宋青州与他灞桥送别。满城章台柳色,缀以零星杏花雨。沾衣欲湿,吹面不寒。彼时宋青州不过是个最正派不过的,所思所想无非天尊,不谙离别苦,单伫立一旁,手头捻枝缠满白绫的灞桥柳。
尘霜和清霜大抵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历经后闲枕案桌时,吹往茶盏里的世味浮云;后者乃雪名一口,道骨仙风。
宋青州望着他,江辞也望着宋青州。清波微漾的千顷江面上,江辞长身立在轻舟一尾,抬起头,似笑非笑望着宋青州,宋青州微微侧头,衬度不出他此时所想,故而低头一笑——
江辞踩上船头,负手而立,指节叩着腰间环佩,依稀是一阕古艳歌。涉江而行,步履缓慢。待他终于来到宋青州面前,万水千山抛诸身后,独一身道袍郎秀于眼前。
缘何不走了,宋青州正要开口发问,却见江辞偏过头冲他一笑,遥遥竖起一指,作了个且慢的口型,朝他迤迤然走来。
江潮拍岸、卷起千堆雪;大风休住、吹往三山去——是江潮絮絮,风声渐起,教宋青州不辨日月,只识得江辞一人。待到江辞终于踱来了,宋青州抬头,手头柳枝一扬,正好教江辞逮住末端白缠。
宋青州单手扣肩,语气间略带打趣。江辞未加以言辞,不过是笑,紧接着便屈膝躬身,衔起白缠一段,从腰间摸出枚环佩,三两下绑将上去。
末了江辞随手一抹嘴,站起身来,眉眼间全是奕奕神采。清风拂山岗,压倒了远山青青荞麦,却不教江辞有半分折腰,反是拢宽了他衣袍,拂乱了他鬓角乱发。
宋青州不由失笑,伸手拭去他额间涔出的点点细汗,江辞却趁势躲过,反手扣住宋青州肩胛,替他斜簪一枝柳色,低声笑道:“这柳色尤其衬你,看起来特别好。”
过栈道,登巉岩,终于于旭日东升时抵了宋青州门前的那棵老松。华山高万仞,松柏须更高。扶摇直上,江辞轻巧地匿于老松枝头,头顶松雪,脚踏枝檐。
不消多时,便见宋青州一身道袍,面目清峻。未入江湖,不知江湖,更肖剑仙。他凝神屏气,两指并拢,抚上剑锋,长身未动而神念先行,一点寒芒先至,随后剑出如龙。矫若惊虹,婉若游龙,长剑所指,千山尽处,白鸟铩还。
他练得极认真,眉目紧蹙,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与雪名一口。待他收剑入鞘,一时四顾茫然,便稽首更向天地,低声念了句“天尊”。江辞斜靠在老松枝头,抱臂坐观,低头瞧他那副清峻样子,忍俊不禁,随手捡了枚石子,掷向宋青州。
待宋青州转头望去,所见便是江辞仰靠在老松遒枝上,手里斜斜捻着支点穴笔,云舄悬空,单手撑着头,略略打了个呵欠,随即便笑道:“想你了,来看看你,你竟才瞧见我,真是让江某人好生伤心啊。”
宋青州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相对,只得摸摸鼻子,颇无奈地瞥他一眼。江辞也不难为他,干脆跳下来,脚一崴,身形就不稳了,险些摔着。宋青州见状连忙上前扶将,眉头紧蹙,生怕他磕着碰着。江辞却不以为意,勾住宋青州脖颈,另手施施然解开鹤鹬大氅,替宋青州披上,呵着口白烟,笑得俊爽。
挺好的一部纪录片,当然不能指望说一部纪录片能拍出一套《中国通史》书的效果来,作为科普来说基本是足够了,同理还有央视以前拍摄的《世界历史》系列,优酷有全集,这里就不贴地址了。
讲先秦文学的时候给学生放映的纪录片系列,仍然是央视的手笔。楚国在先秦诸国里是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楚庄王问鼎中原以前,楚国处在诸国中最边缘的一个地带,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以外;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那个能够亡秦的又为何一定是楚国呢?每个人都会在这部纪录片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挺好的一部纪录片,当然不能指望说一部纪录片能拍出一套《中国通史》书的效果来,作为科普来说基本是足够了,同理还有央视以前拍摄的《世界历史》系列,优酷有全集,这里就不贴地址了。
讲先秦文学的时候给学生放映的纪录片系列,仍然是央视的手笔。楚国在先秦诸国里是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楚庄王问鼎中原以前,楚国处在诸国中最边缘的一个地带,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以外;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那个能够亡秦的又为何一定是楚国呢?每个人都会在这部纪录片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观《史记》,前有《项羽本纪》,为败者著书,为败者,又为败者将他的败因一一数落。党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太史公却为一个败者著了“本纪”。
又有《李将军列传》,前后排布,澎湃,义者便写义,龃龉者便写龃龉;将军的优劣都跃然纸上,这也是所谓的“不虚美,不隐恶”。
还有《卫将军骠骑列传》,与《李将军列传》前后对照,本身虽然在史学上存在争议,但亦是司马迁个性的一部分。
《史记》是我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在它以前,史书或以年代排布,或以国家区分;从来没有一本像《史记》一样,把人从历史灰色的背景中掏出来,把人放在舞台上,把人放在笔的中心,以人的人生去交织成历史。
历史本身就是由很多个人的人生组成的不是吗?只不过,当太史公把目光投向每一个人的时候,历史开始有了温度。
司马迁极刑,几欲就死;《报任少卿书》,洋洋洒洒一大篇,饱蘸着他的恨和,故而能使悲恸之情贯穿全篇,即使几千年后的人去观之,依然不禁怆然而涕下。
他把这些感情都灌注到了《史记》里。身体上的残废让他的感官变得愈发敏锐,让他的言辞愈发犀利精准。他写历史里的人,写他们在下的、在皇权下的、在逆境或顺境里的,他写的不是人物,也不是历史,是他自己的恨、希望、、悲哀、痛苦。这是来自几千年前文人的主义,以致于那些喜爱《史记》的人,看的不是参悟,是人生的痛和寂寥。
玄奘之所以要去取经,乃是因为当时大唐所保存的经卷里有诸多纰缪,所以他需要去“取”。他偷偷地去,背着一点行头,蹒跚了十七年。这是发了大愿的才会做的事。求真之上,他的身边并没有什么徒弟,有的只有他对的向往。
“公元1644年,这一年的春节是大明王朝崇祯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新年。元旦一大早京师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大风霾在古代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征象乃大凶之兆。1644年的春节,作为帝国最高者崇祯比任何时候都真切地感受到大厦将倾的悲剧已经成为不可的事实。三个历史关键人物: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改写了历史。”
“请建造一个,材料用大理石,用美玉,用青铜,用瓷器,用雪松做这个的房梁,上上下下铺满宝石,披上绫罗绸缎,这儿建,那儿造后宫,盖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又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总而言之,请假设有某种人类异想天开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而其外观是神庙,是,这就是这座园林。”
这应该是我去年看过的最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系列了,它的风格非常奇巧,从电影的台前看到幕后,看见电影背后的一整个时代;它的意义不仅止于电影,还在于它深沉的史观。
这个系列是凤凰卫视做的,主要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台前幕后的事情,地区好像找不到在线资源,可以找找看有没有网盘下载,或者在YouTube搜索观看。
这个好多期了吧,哎呀我看不全……有兴趣的还能跟《鉴宝》节目交替着看,对就是那个时不时会有人捧着青花瓷开水瓶上来的节目……
这是1958年拍摄的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录片……由于拍摄年代背景的,里面解说词可能会让人有些不适,但本身仍然是珍贵的视频素材,看的时候不要激动,要理解……
非央视、非制作的纪录片里所采用的视角可能会跟我们以往所受教育中惯有的不太一样,看个人要如何接受了。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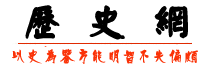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